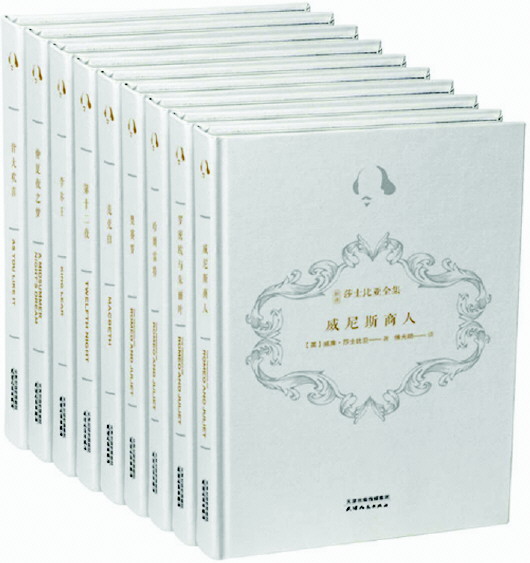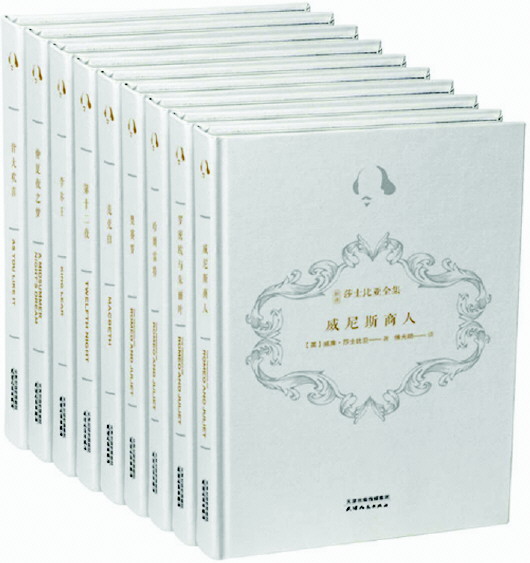
《新译莎士比亚全集》
莎士比亚 著
傅光明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
一入“莎门”深似海
自1902年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首次将Shakespeare译成“莎士比亚”,莎翁在中文世界便有了固定的称谓,一代又一代莎翁译者也将不同的中文译本呈现给中国读者。正如翻译家陆谷孙说“发现莎士比亚是个永不停歇的进程”,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方平、辜正坤等人翻译莎剧同样是个永不停歇的进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与国内大多数读者一样,傅光明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朱生豪的译本步入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十多年后,到90年代中期,梁实秋的莎翁全集译本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读了梁实秋译本,傅光明发现了许多跟朱生豪译本不同的地方,并产生了疑惑:莎士比亚为什么会讲两种中文?那时,恰巧恩师萧乾送给他几本莎士比亚作品英文单行本小册子,中英对照着看,他发现了问题所在。朱生豪、梁实秋都是杰出的翻译家,但由于身份、工具等主客观问题所致,二者的译本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朱译本“美而不信”,梁译本“信而不美”。
“每个译者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莎翁,每个时代都呼唤着它的新译者。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莎翁译本。”从2012年起,他从老舍研究转向,开始以一己之力重新译莎、释莎,以前是“逢人开口谈老舍”,现在是“逢人张口聊莎翁”。
为了更好地翻译莎士比亚,傅光明到英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独自闲行”,去了莎翁故乡斯特拉福德小镇,去了莎翁受洗并安葬的圣三一教堂,还在莎士比亚时代经常上演莎剧的“环球剧场”看了两部莎剧,其中一场《无事生非》买的站票,在圆形剧场的露天院落里站了三个小时,体验底层观众的看戏感受。
傅光明意识到“全译莎翁”既要有充沛的脑力,也要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支撑,因此近些年开始坚持长跑,“新译莎翁本身就是一个人的马拉松,唯有像一只小蚂蚁勉力前行,才可能跑过终点。我正在途中,刚刚跑过三分之一,前路还很艰辛、漫长”。尽管目前只出版了第一辑、第二辑(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皆大欢喜》《李尔王》《第十二夜》《仲夏夜之梦》),距离“全”还有一些距离,但傅光明表示会在前辈们卓越的积淀基础上,努力地站得更高一点、走得更远一些。
莎士比亚或许并没那么伟大
相比于很多人把莎士比亚想象成一个创造力无限的原创型天才戏剧诗人,傅光明眼中的莎士比亚没有那么伟大,他将自己的翻译和研究对象称为“巨大的难以超越的莎士比亚现象”,努力为读者呈现一个打开的、多元的、开放的莎士比亚世界。
莎士比亚刚开始写戏的时候,并不出名。但他幸运地出生在伊丽莎白时代,这是一位喜欢诗歌、露天剧场并把剧团请进宫廷演出的“文艺女王”,她的时代是英国文艺复兴的繁盛期。他的幸运还在于,当时英语拼写、句法都不规范,同时代很多作家,包括莎士比亚在内,写的东西在今天看来简直错误百出,却被当作正确的范例存在下来。
作为一个乡下来的“伦敦漂”,莎士比亚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写戏、上演、赚钱,即便做了剧团的股东兼编剧,其走红程度还是比不上剧团里的台柱子演员。戏迷买票看戏,不是因为莎士比亚的影响力,而是剧团中首席喜剧演员威廉·坎普的丑角表演和吉格舞。莎士比亚不得不对角色和剧情做出修改,比如为了充分体现坎普的表演才能,硬性插入由他表演的对某段正剧情节的戏仿、恶搞,或是突兀地跳上一段与剧情几无关联的吉格舞,就连《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彼得、《威尼斯商人》中的兰斯利特·高波等丑角也都是为坎普专门设计的。
有时写戏只为一个剧团跟另一个剧团竞争,比如当时的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有个剧本《马耳他的犹太人》非常卖座,莎士比亚很快为自己的剧团打造了一个剧本《威尼斯的犹太人》,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威尼斯商人》。
莎士比亚的戏剧,并非为读者所写,也不是为了当经典流传而写,只是为了那个时代的人能到剧场观看而写的。所以说,莎士比亚的身份首先是一个剧团的签约作家。1594年,莎士比亚与伦敦一家顶级剧团——内务大臣供奉剧团签约,每半年写一部新戏,并由剧团尽快上演,演出卖座,剧团才能赚钱,他作为剧团的股东之一,也能分到不少红利。
莎士比亚如何能够在半年间又快又好地写出一部戏?如何在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写出37部能够流传后世的作品?傅光明在专门论述莎剧素材源流的《莎剧的黑历史》一书中指出,与同时代的编剧一样,“莎士比亚从不原创剧本,而总是取材自古老的故事”。傅光明考证出与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相关的七种历史文本,不仅如此,几乎所有莎剧都不是原创,每一部都几乎有一两个甚至更多的素材来源和故事原型。再加上为了迎合观众,其早期的作品有些通俗甚至低俗,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后世作家托尔斯泰、萧伯纳等人毫不留情的毒舌攻讦。
尽管莎剧非艺术原创,若放在今天,或许还难逃抄袭、剽窃之嫌,但在傅光明看来,莎士比亚能够集聚各文本之长,再加上天才的创造力,几乎他的所有作品都健康地“活”了四百多岁,他的“四大史剧”“四大喜剧”“四大悲剧”皆成经典,从而凸显出莎士比亚卓越的艺术才华。反倒是那些被莎翁“借来的”“前辈的戏剧、编年史剧和短篇小说”,随着时间的淘洗,都已悄无声息,从而验证了“天长地久,莎翁不朽”!
生前,莎士比亚对出版剧本毫无兴趣,他本人没有确定过一个剧本出版。今天通行的中译本的源头,大多来自莎士比亚去世7年之后的1623年,由他的朋友兼同行为他编辑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也就是著名的“第一对开本”。正如耶鲁大学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卡斯顿教授评论的那样:“虽然莎士比亚从未追求过伟大,但他逝世七年之后,伟大找上了他。”
研译合一的“原味儿莎”
莎士比亚的好友、同时代剧作家本·琼生称他为“时代的灵魂”,德国诗人海涅将他比作“英格兰精神上的太阳”,马克思称他为“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之一”,雨果赞美他的戏剧是“文化的熔炉,人类默契的交汇点”……长期以来,对莎士比亚剧作的极高评价,使之已然成为高雅文化、纯文学的代表,不少莎剧中译本采用诗歌体翻译,追求文字风格典雅精美,以符合莎剧作为文学经典高峰的地位。
然而在莎翁生活的时代,他只是一个烟火气十足的剧作家,他早中期的戏剧大都是演给下层民众看的。傅光明开始思考:“翻译语言是否要选用高贵文雅的漂亮中文?朱丽叶的粗俗的奶妈张口说成语是否妥帖?今天我们该如何替莎士比亚说中文?”
傅光明注意到,莎剧中有不少对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名、典故、故事的借用或化用,以及许多双关语的妙用。除此,一些用词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并暗藏着隐晦的真意。这在朱生豪译本中几乎没有体现出来,这自然是因他翻译时的客观条件所限。同时,朱生豪译本和梁实秋译本这两个通行许久的版本,其中有许多译文表述方式,尤其欧化句式、倒装语序,已不完全适合现代年轻人的阅读习惯。
尽管译介莎剧的译者都是出自英文系,中文系出身的傅光明依然对自己的译笔充满信心,恩师萧乾曾告诉他,翻译时“理解占四成,表达占六成”。就像许多人喜欢原味酸奶一样,傅光明希望能够在风格各异的众多版本之外,努力呈现出一个“原味儿莎”,以今天的现代语言呈现莎士比亚时代的语境。他首先将莎士比亚定位于一个有着浓浓的尘俗味道的“人间莎翁”,译本文体采用诗体译诗、散体译散,但在“散体译散”的时候,特别在意能否译出散文诗的韵致,让语言具有一种诗的内在张力。“它不一定押韵,却内蕴诗的魅力。”
傅光明特别指出,“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剧”,莎士比亚把从《圣经》里获得的艺术灵感,巧妙地折射到剧情和人物身上。他以《哈姆雷特》举例,克劳迪斯向国人撒谎说是一条毒蛇咬死了在花园睡觉的老国王,以掩盖其篡位真相,而老国王的鬼魂则在嘱咐哈姆雷特复仇时咒骂说:“那害死了你父亲的蛇,头上戴着王冠呢。”这里出现的两条蛇,一条是自然界的蛇,另一条则是“头上戴着王冠”的魔鬼撒旦。傅光明说,如果没有注释,没有领略莎剧中无处不在的《圣经》意蕴,对于理解莎翁必然会打折扣。
如今,除了早期版本,英语世界还有许多为莎迷所熟知且津津乐道的莎剧全集,比如颇具代表性的“皇家版”“新剑桥版”等版本。因此,若想真正步入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从阅读上来说,势必离不开丰富的注释。除了注释,傅光明每新译完成一部莎剧,会专门写一篇上万字的专业性导读附在书中,其中包含了他在莎士比亚研究中的许多新发现。
前不久,傅光明偶然间发现抖音上两段关于莎士比亚的视频节目,简短有趣又“有文化味儿”,相比之下,面对博大精深的莎翁戏剧,大多数人总会有肃然起敬却读不下去之感。傅光明认为普通读者对莎剧有畏惧感,跟语言有关,“我的责任就是帮助当代读者跨越语言和文化差异的障碍,走进莎翁的戏剧世界”。
本版编辑:曲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