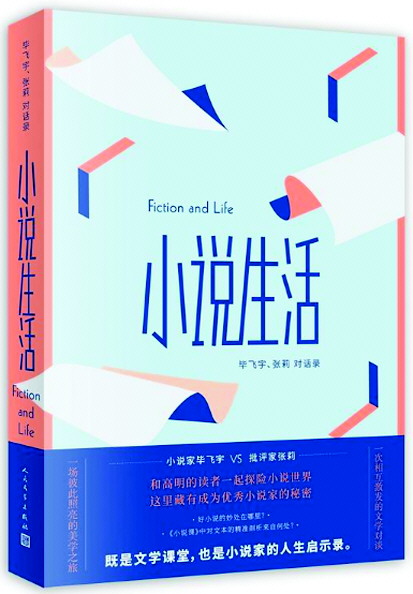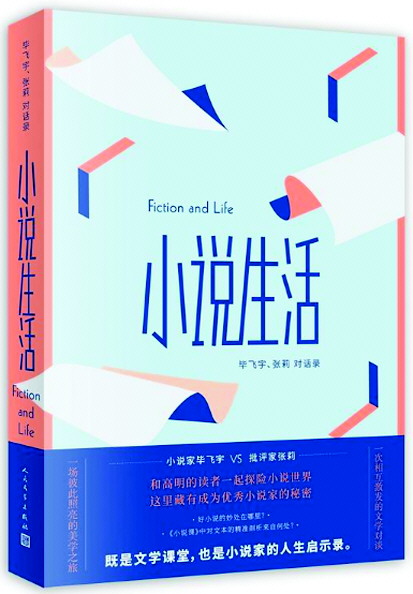
《小说生活》
毕飞宇 张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毕飞宇:我在大学时代读梅特林克,他的《青鸟》一棍子就把我打晕了,那是完全脱离了日常的戏剧文本,人所面对的只有两样东西,时间,还有空间。一个人死了,一百年之后,他的爱人出生了——这多牛啊。我热爱这些理念,它们让我着迷。这里头还有我的虚荣,年轻人的虚荣,艺术是不该和散发着体气的日常生活沾边的,咱们得到远方去寻找描写的对象。
张莉:当时的年轻人眼睛都朝着天,不落地。
毕飞宇:后来就开始接触中国的先锋小说了,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通常说来,中国的先锋小说脱胎于西方的现代主义,就时空的处理方式而言,也许是的,其实,说中国的先锋小说脱胎于西方的浪漫主义也许更合适一些。“浪漫”这个词在法语里头其实就是逃避的意思,逃避什么呢?逃避现实,不再现实,结果就是浪漫。
张莉:这个说法有点新意。
毕飞宇:反正我尝试着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一点现实的东西,日常生活那就更不用说了。但是,一个写作的人不可能恒定不变,他会调整自己,他会认识自己,同时也会认识文学,这里头既有修炼的问题,也有一个年纪的问题,人都要长大,伴随着长大,你对生命的认知、对生活的认知、对表达的认知,都会变。
张莉:生命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修为、不断完善。我也有这种体会,以前反对的,反而成了现在热爱的,一百八十度转变。
毕飞宇:老实说,当我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注重日常问题的时候,我在骨子里是痛苦的。大约在十年前,中国文坛开始时兴一个词,叫“后撤”,一个人在后撤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带着一些不甘,这个不甘会带来痛苦。我从此知道了一件事,我再也做不了仙风道骨的艺术家了。我当时的痛苦很具体,一方面,在理性上,我知道自己必须往那里走,另一方面,情感上不愿意。我的许许多多的痛苦就是这么来的,不止这一件。
张莉:同时,你也开始发现,跟日常伴随的就是伦理,人情的伦理,用你的话来说,文学要有“俗骨”。一个好的小说家,离不开这个东西。
毕飞宇:小说总是离不开两样东西的:第一,它的美学属性,也就是审美价值;第二,它的功利性,也就是社会意义。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俗骨”,他的作品就无法支撑社会意义。王彬彬有一本书,书的名字我非常喜欢,叫“在功利与唯美之间”。要知道,在功利和唯美之间,作家是很纠结的。我没有和别人交流过,但是,我纠结,骨子里,做一个小说家是很难幸福的,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让他纠结。
写日常更考验作家水平
张莉:其实我总觉得,写日常对一位作家是个考验,以大开大阖的剧烈命运吸引读者不难,如何写出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戏剧性”是一个挑战。现实,日常,怎么也不该成为一位作家的盲点。
毕飞宇:是这样的。
张莉:这种世情伦理在你的小说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特征,尤其在读《平原》的时候,我当时写评论,觉得两个农村妇女之间的那种说话非常有意思。它其实传承了中国明清世俗小说里面的某种精华。
毕飞宇: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老作家,《平原》刚刚发表,他见到我的时候,说《平原》里面有一部分写得特别好,我说哪个部分,他就说端方的妈妈去找会计的时候,她的手上拿了一只酱油瓶,到了会计家的门口,她把酱油瓶放在了地上,然后,空着手进门了。
张莉:她这么做是有她的缘由的。
毕飞宇:我们乡下的女人心是很深的,她要托人办事,一般不会直接说,而是找一个借口,仿佛是路过,临时想起来的。为什么要找一个借口呢?因为她没把握,怕人家拒绝,如果是路过的,被拒绝也就不伤脸面了。到了家门口,她要避免误会,别让人家以为是送礼来的,所以,就把一个空瓶子搁在了天井的地上。——这一来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张莉:心思缜密。透过这样的细节,这个人物跃然纸上。
毕飞宇:作家要塑造人,第一件事是理解人,从哪里理解?从日常生活这个层面上理解。如果没有这个酱油瓶,端方的母亲这个行为就很难饱满。刚才我们说了半天的人物,现在又来谈日常,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你不在日常上下功夫,所谓的塑造人物往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同样,如果这个日常不通过人物的动态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日常就很难散发出它的魅力。
张莉:重要的是,书写者不能浮在生活的表层,浮在生活的表层是看不到那些细节的,只有当作家浸入生活,沉潜下来,这些细节才会信手拈来。因为这种日常,这小说脱离了1976年这个背景,还会被读者理解,因为,我们今天还有这样的生活习惯,或者是这种人与人交往的方式。
毕飞宇: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平原》当中描写那么多的日常生活的细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些细节呈现中国农业社会时期的基本伦理。这是第一层。为什么写这个基本伦理,我要告诉大家,无论“文革”的政治多么惨烈、多么残酷,它永远没有能力去替换生活的基本伦理。说起来我还要感谢张爱玲,她的《倾城之恋》我读过很多次,张爱玲不是一个做史学研究的,但是,她的这个大历史观对我有启发,无论飞机大炮多么热闹,影响不了基本生活的格局和底色,生活里那些必需的部分,它们永远在那儿。
张莉:历史的某一个层面,就是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历史有它普泛性的一面,或者说是肌理。以前批评界喜欢史诗作品,以为只有写大事件才是写历史,其实不是,日常本身也是历史,另一种恒常的历史。
毕飞宇:1976年发生了那样的巨变,我想说,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不是政治,还是日常的伦理。我不懂政治,但是,有一句话我觉得比所有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理论都有力:“生活就应该这样,生活就是不应该那样。”这里头有常识性的、铁一样的价值观。
(选自《小说生活》,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