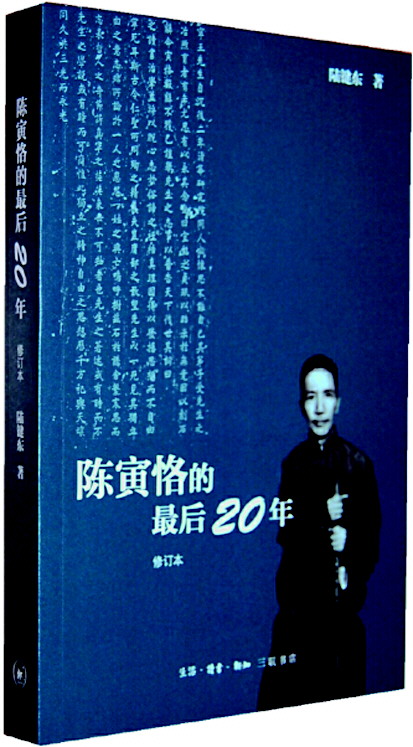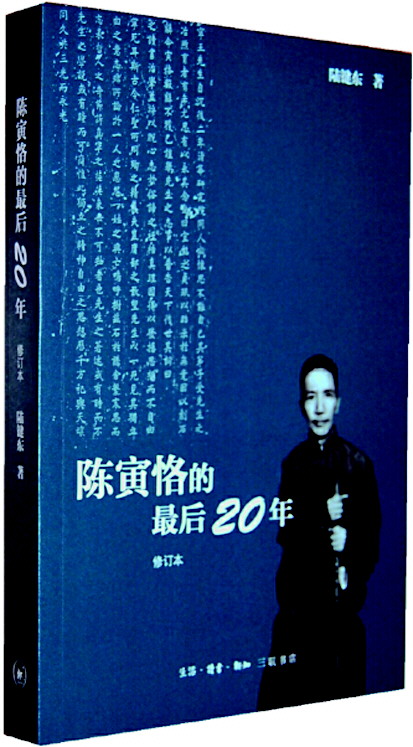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陆键东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陈寅恪的学说》
刘梦溪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多年前,一部《陈寅恪的最后20年》,将研究冷门绝学的陈寅恪推向了神坛。从民国学术的风骨与标杆,到充斥着八卦和琐事的传记文学,再到错漏百出、刻意拔高的网络段子。神化后的陈寅恪,已经离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渐行渐远。
离开这个世界50年里,他被附加了太多。其实,陈寅恪是个简单人,是个纯粹的“书虫子”。生前尚且不为名利所累,死后又何必拿各种框框扣住他呢?
留洋不带学历归,学问只在兴趣间
读懂陈寅恪的经历,才能真正明白他的人生。
陈寅恪生于1890年,老家是湖南长沙。他出生的时候正值庚寅年,所以家人为他取名寅恪,“恪”为家族兄弟间的排辈。
这是一个家世显赫的书香门第。祖父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是戊戌变法中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父亲陈三立与谭延闿、谭嗣同并称为“湖湘三公子”,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为“维新四公子”,官至吏部主事,是晚清著名的诗人,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
生在诗礼之家,陈寅恪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但与梁启超、王国维等同时代学术名宿不同,陈家家风开明,家中学堂采用的是现代教育,教授四书五经的同时,还开设了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
当时,陈三立与教师们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陈寅恪自幼便在这样一种宽松的教育环境中成长。陈寅恪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对他而言,读书从来都不是一件功利的事。
今天,人们觉得陈寅恪多少有些遗老遗少的晚清文人做派,殊不知,他很早就受到了洋风熏陶。出国留洋这件事,对他来说轻车熟路。
1902年,陈寅恪第一次出国,那年他才12岁。陈寅恪随长兄东渡日本,到弘文学院学习日语。此后两次赴日学习,直到1906年,陈寅恪因病回国,就读复旦公学。20岁后,他又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后来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于形势,才于1914年回国。
28岁时,陈寅恪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学习了3年之后,他又由美国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以及蒙古语。
这种学遍东洋和西洋的经历,在那个大变革时代中亦不多见。可有意思的是,虽然出国游学二十多年,但是陈寅恪却未怀揣一张高级学位证书回来。倒不是他水平不够,而是他完全为了学知识而读书,不在乎这些“纸”。
看看陈寅恪在海外学的东西就会发现,“经世致用”这个词跟他几乎不沾边,冷得不能再冷的“死文字”倒是学了一大筐。他在留学期间的想法是,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多,他便去哪里读书。只要自己感兴趣,再冷门、再“无用”的知识,他也愿意去下一番苦功夫。
学位对他而言真就是一张纸,没什么价值,装到脑子里的知识,才是真真切切的收获。对他来说,政治、现实、权力甚至儒家的士大夫情怀,都只是过眼云烟,提不起兴趣。这种洒脱、非功利的学习态度贯穿了他的一生,是陈寅恪与其他同辈学者最大的差异。
他的骨子里或许只想做个扎进书堆的爱书人,然而实力却不允许他继续低调下去。1925年,36岁的陈寅恪回到国内,正赶上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得吴宓力邀,没有博士学位的他,破格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执教,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成为四大导师。
陈寅恪属于博闻强识型的,天生记忆力好,看过的知识基本都能留在脑子里,而且能随时调取。做到这点,确实是需要天赋。1946年,吴小如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就读,选修了陈寅恪的《唐诗研究》课。吴小如每次见陈寅恪,必带去一堆问题。陈寅恪听过之后,总能语调轻缓、从容不迫地回答。特别是有些人物传记和典章制度,陈寅恪能随口列举出在新旧唐书的某卷某传或某志某条。吴小如回来检索时,十之七八都能找到答案,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
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让人们记住了陈寅恪。上世纪九十年代,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风行一时,陈寅恪作为知识分子人格的象征,被捧上了神坛。自那之后,关于陈寅恪的各种神话、谣言漫天飞,然而,对他的学问,人们却关注很少。
得益于天赋异禀的记忆力,陈寅恪治学面广,对宗教、历史、语言、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见解。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可是爱讲课的陈寅恪,似乎懒得动笔写文章传之后世,著作数量着实少得可怜。他的代表作主要是“四稿一传”,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从书名可以看出,陈寅恪对名震天下的“四稿”并不太满意,甚至只能算是草创而成的授课讲义。
陈寅恪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西思想和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提起《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都会竖大拇指,这与陈寅恪中西兼容的治学风格密不可分。
陈寅恪的著作大都是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之类,他总是习惯于先引上若干条史料,然后再加上一段按语的做法。给人的感觉,他的文章更像是没有经过深加工的读书札记,更谈不上有多少文采。可是,看似冗繁的文字中,陈寅恪又有自己的特色。
中国古人搞“抠字眼”的研究已经两千多年,钱大昕等清代乾嘉学者更是将考据这门功夫演绎到了极致,几乎成为不可逾越的高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寅恪硬生生给考据开辟了一条新路。
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中西结合考证比较。在这个基础上,他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像侦探破案一样,从事物的细微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这种精密考证方法,代表着时代的进步,为后来学者所继承。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种考据方法。他首先注意到,除去文学的外衣,唐诗中蕴藏着海量的史料。在他看来,唐诗的作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唐诗中许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现实生活,可以补正正史之不足及讹误。与此类似,小说等过去被历史学家认为“不入流”的一些文字材料,也被陈寅恪纳入了史料的范畴,这比前辈学者又技高一筹。
中西碰撞出火花,字眼抠出了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