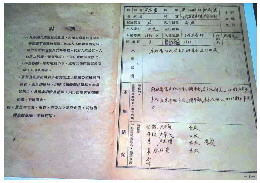2019年93岁的老党员毛连卿与作者

74年党龄的老党员孙振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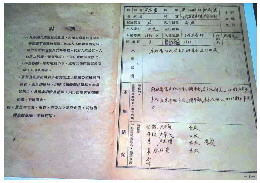
老党员尹志贵1944年的入党申请书
□姜成娟
6月23日,莒县本色老党员红色群落展览馆。这个下午,讲解员在为前来学习的党员们讲解,作为馆长的我,观察着大家的反应,在老党员薛贞翠的视频资料前,我的眼睛依然酸楚。我的眼光温柔地抚摸过视频中老人倔强、沟壑密布的脸,我热爱、理解他们,每一个。我几乎把一生最多的热爱,给了这个群体——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
是的,我把自己最美好的7年时光,奉献给了“本色”,奉献给了这个群体。
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在广阔田野中的展览馆?
1949年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意味着什么?危险和牺牲。而农村里这些老党员的特征是,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之后没有进城工作,在漫长的岁月里,战功累累的他们一直在农村耕种、生活。他们之中,最大的官是村支部书记。他们在最基层,用衰老的身体,变形的手指,不变的忠诚,维护着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巩固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们的政治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的社会身份是普通农民。
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于沂蒙老区的我,与很多同龄人一样,历经升学、就业以及在现代城市繁忙工作与家庭育儿之间的矛盾等过程。我开始思考,当代女性困境的根本源头是什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国家的产生》指出:一切现代家庭都建立在女性隐形家务奴隶的基础上。那么,女性的解放怎么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于每一个在世界上活着的生命,意义是什么?
作为八零后,我们甫一出生,就与市场经济劈面相逢,让我一直在思考并疑虑的是:当很多人把占有金钱的数额当作了生活的目标与价值,当人们把这些指代了生活的意义,那么,生活除了房子、钱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活着的意义?除了房子、钱之外,还有没有一种可以被当作人生要义的东西?我们要不要追求有意义的人生?而它该如何定义?
到2014年的那个夏天,我觉得,我找到了答案。
薛贞翠1942年15岁时入党,到结婚时,已经是有7年党龄的党员了。结婚前,她风风火火做工作,生活充实而愉快。结婚后,她遇到了问题:她的丈夫、丈夫的父母都让她退党。原因很简单:影响做家务。她抱着孩子开会,回家后,家门紧闭。她和孩子蜷缩在门口睡着了。第二天,丈夫家通知她:要么退党,要么离婚。薛贞翠很平静地回答:“就是去要饭,俺也不退党。”
在那一批老党员中,对当时的我,引起最强烈感触的,莫过于她。因为我当时最大的困扰,就是工作与照顾孩子无法兼顾,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当代社会出现很多全职妈妈的直接原因之一,也是女性在当代所遇到的较普遍的社会问题。
薛贞翠的遭遇,又是多少女性的遭遇?女性的成长、社会属性,什么时候才不受到尿布、孩子的羁绊?为什么女性要成为自己,要行使最基本的工作权,如此之难?这也是我后来读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时,醍醐灌顶般狂喜的原因所在。
薛贞翠的这段视频资料,存放在本色馆里,当我在这里工作,济南的家里,孩子各种问题无法解决、无法两全时,我经常一个人打开这段视频,伫立良久。
棋山小河村老党员刘太花也是如此。16岁入党的她,还把自己的父亲介绍入党。她17岁结婚,在外开会,回家也是遇到同样的情况:不开门。她就喊:“你们听着!就是死了,我也不出党!”那是1941年,根据地最困难的时候,家里的情况是:公公是党员,丈夫的哥哥已经牺牲,姐姐也已经牺牲,代价太大了。是的,老根据地的人民,牺牲实在是太大了!此时她的公婆不让她再出去工作,可是她倔强地不答应。做军鞋,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她总是几倍完成。没有布料,她就使用自己家的床单、衣服。
什么是最后一尺布做军装,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这没有任何的夸大,这就是老根据地人民对党、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完全无私的支援。
张维兰,1944年入党。她的父亲也是共产党员。张维兰12岁就为党送情报,她把情报藏在棉袄里,过封锁线据点。她结婚后,就把情报藏在孩子的襁褓里。我问她:你不害怕吗?她说,要是人人都害怕,那共产主义怎么办呢?
共产主义,这个词语在庸碌日常的生活里,已经离开我们多久了?我没有想到,是在老家的土地上,我听到了它。
在老家的田野、柴垛边,他们太寻常了;以至于在我生活在那里的那么多年,忽视了他们。不仅我,在太多年里,太多人,忽视了他们,忽视了他们的光芒和价值,也由此承受了这种遗忘和忽视的代价。
还有一位叫崔立芬的老人,她并不是党员。共产党员王涛把孩子寄养在她家,粮食不够,她的奶水很少。她每次都先喂王涛的孩子,自己的亲生女儿饿得大哭。她对孩子说:我得先喂党的孩子,党在给咱打鬼子啊。
我也是母亲。那天我问自己:我能不能做到?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答案是:党在给咱打鬼子。党为我们,我们为党。打鬼子,是大,是共同的事情。他们,就是从这个“大”出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这是我第一次开始不是从“我”出发,来考虑问题;而是从党,从事业,从“大”,来考虑问题。这个“大”是什么?“大”,就是崇高,是不汲汲于自己的个人境况,是融入党的事业,是牺牲与奉献……
我的外公商学周,1944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进城工作,妻子在老家病重,托人带信让他回去,他正带人在全县架设电线,等他忙完工作回家,妻子已经去世。我曾经无法理解外公。工作比家人生命更重要吗?有一天,我在一个叫许世斌的老党员家中寻访时,听他儿子说,三年困难时期,许世斌是食堂主任,他却坚持遵守规矩,不肯让病重的父亲先打饭。
在那一瞬间,我终于理解了我的外公!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回家?为什么拼命工作?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因为他们是在用一颗颗赤诚的心,在为这个党,为这个他们用命捧出来的新中国努力工作啊!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
几年里,当我奔波在莒县与济南之间的长途客车上,闻着公共交通工具上各种混杂的味道,当我在宿舍里书写他们,蚊虫叮咬,虫声唧唧,支撑我的,正是这一点点可以被称为崇高的东西。
当我一个人在展览馆几层楼的空间里,用目光抚摸老人们的脸,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和这个馆是一体的。这就是我舍不得走的原因啊!
几年里,我切实地看到了在我脚下这片土地上,在今天的中国基层,大量普普通通的党员干部在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着;他们传承的,就是本色精神。老党员们创造的本色精神,在今天得到了传递和继承。
送走又一批学员,我在馆前抬头,落霞明亮,橙色的天空一片辉煌。正如今天的我,坚定、不惑、澄明、追求崇高以及践行崇高,格局与精神上的高蹈、超拔,的确能够带给人外表上的改变。它表现为:明亮、广阔、坦荡。这是我的切实体会与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实。
在我们向着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过程里,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一百年之际,一个普通中国青年曾经经历过困惑、迷茫,并最终寻找到了这个方向与道路;我相信,我的困惑,也是很多中国青年的困惑;我走过的追寻的道路,也会是他们的道路,一个新时代青年的信仰之路。
姜成娟:莒县本色老党员红色群落展览馆馆长,作家,省青年作协副主席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