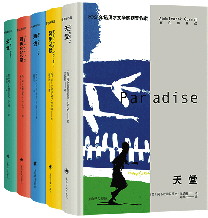□刘国枝
2018年春,我译完丹麦作家伊萨克·迪内森的 Out Of Africa 全书后,为中文书名纠结良久。Out of Africa 的字面意思是“在非洲之外”,就作者的创作实际而言,是“在非洲之外(丹麦)”回首往事,从作品的内容来说,也是“失非洲”“忆非洲”或“非洲梦回”,是身在非洲之外而心却仍系非洲,因而从根本上展现的恰恰是一个“走不出的非洲”。但由于《走出非洲》之名已经在一代代读者中深入人心,特别是通过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电影而几乎变得家喻户晓,思虑再三,我决定沿用旧名,也算是致敬经典,并在译后记中对此做了说明。
在随后一年半的时间里,由于工作关系,我两次走进非洲,也到访过肯尼亚,虽无暇前往保存完好的迪内森故居参观瞻仰,但在公务之余,我有幸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仰望清澈寂寥的夜空,并观察各色人等熙来攘往,常常不自觉地脑补迪内森描写过的画面,耳边仿佛还萦回着作家的不舍追问:“如果我会吟唱非洲之歌,吟唱长颈鹿,以及照在它背上的非洲新月,吟唱田地中的耕犁,以及咖啡采摘工那汗涔涔的脸庞,那么,非洲是否也会为我吟唱?草原上的空气是否会因为我身上的色彩而战栗?孩子们是否会发明一个带有我名字的游戏?圆月是否会在碎石路上投下像我一样的影子?恩贡山上的鹰是否会找寻我的踪影?”我吹着迪内森吹过的风,不禁暗暗感慨自己与非洲的交浅缘深。
2021年10月7日,瑞典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籍坦桑尼亚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以表彰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的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11月初,我接受了《天堂》的译事,这部作品源于作家1990年的一次东非之旅所激发的灵感,于1994年出版后入围布克奖。就这样,我得以再次走进非洲,走进古尔纳笔下那个全然不同于我既有印象和想象的非洲。
《天堂》首先是一个关于小人物的小故事,是其亲身经历和亲耳听闻的故事,正如开篇所言,“先说那个男孩。”十二岁那年,斯瓦希里男孩优素福离开父母,跟随阿齐兹叔叔乘火车前往海滨城市。阿齐兹叔叔是一位富有的阿拉伯商人,此前带领商队前往内陆做生意时,常常在优素福父亲经营的小店歇脚,并在优素福家里用餐,他每次出现总是穿着飘逸的薄棉长袍,戴着绣花小帽,身上散发出一股香气,一副友善、从容、儒雅的样子,每次到来还会给优素福一枚硬币,所以优素福对他的来访总是充满期待。这次突然离家令优素福感到惶恐不安,他对此行的目的、期限和前景一无所知,但还是服从了大人们的安排。抵达阿齐兹叔叔家后,优素福成为其店铺的一名帮手。店铺伙计哈利勒年长他几岁,一边好奇地打探他的旧生活,一边热情地指导他的新生活。他们朝夕相处,白天在店里工作,夜晚则睡在主屋前的露台上。哈利勒以“过来人”的身份,教他工作技能和人情世故,并给他讲述各种故事。哈利勒告诉他,阿齐兹叔叔不是他的“叔叔”,而是“老爷”;优素福与哈利勒一样,都是因为父亲欠了债而被抵押给阿齐兹叔叔,成为他的免费劳工,直到他父亲能偿还债务——而这种希望十分渺茫。在对被遗弃的恐惧和迷茫中,日子一天天过去,优素福渐渐长大,并跟随商队前往内陆和深入腹地,了解了人性的复杂和丑陋,目睹了生之苦难和死无尊严。与此同时,由于相貌英俊,他受到许多人各怀心思的关注,不仅受到男人女人的捉弄骚扰,还几度成为人质,甚至险些成为迷信献祭的对象。而阿齐兹叔叔的太太祖莱卡对他更是贪慕已久,多次提出非分要求,被拒绝后便恼羞成怒倒打一耙。优素福五六年来的生活一直是被设计、被交易、被摆布、被需要,他始终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到这时,他得知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已搬走不知所踪,而他心仪的姑娘——哈利勒的妹妹阿明娜——则已成为阿齐兹叔叔的妻子。他不愿再寄人篱下忍辱偷生,但思来想去,却发现根本无处可去。两难之时,一位德国军官率领本地士兵来抓人充军,士兵们在院子周围留下了垃圾和大小便,在他们离开后,优素福看着抢食粪便的狗,仿佛看到了自己,就在那一瞬间,他终于听从内心的声音,拔腿朝渐渐远去的队伍奔去——他毫无“政治正确”的概念,只是终于自己做主,奔向不可能更糟的未来。
《天堂》显然更是一个关于大环境的大故事。坦桑尼亚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早在公元前就与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等地有贸易往来,后来相继经历了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的大批迁入。十九世纪中叶,欧洲殖民者入侵,1886年,坦噶尼喀内陆被划归德国势力范围;1890年,桑给巴尔沦为英国“保护地”,1917年11月,英军占领坦噶尼喀全境。《天堂》所呈现的就是一幅殖民阴影笼罩下的画卷。优素福八岁时,父母之所以从南方搬到一个名叫卡瓦的小镇经营一家旅店,就是因为德国人在修建一条通往内陆高原的铁路线,并把卡瓦设为一个站点,使小镇迅速繁华起来。但随着殖民者的不断深入,小镇的繁华昙花一现,旅店的生意每况愈下,优素福的父亲渐渐债台高筑,终至将儿子抵押给商人而酿成家庭悲剧。十二岁那年,优素福在火车站的站台上首次见到两个欧洲人,而在到达阿齐兹叔叔家之后以及随商队在内陆四处辗转的过程中,他听到许多关于欧洲人的传说,比如他们身穿金属衣,可以吃铁,他们的唾沫有毒,可以死而复生等等,也目睹了欧洲人的明火执仗耀武扬威:公然霸占原住民的土地,掠夺当地的资源,抢走商人的商品等。殖民者的到来改变了坦桑尼亚的社会形态,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成为常态,宗教矛盾、文化冲突和部落相残也随处可见。小说透过优素福未经世事而不加滤镜的视角,将其个人的小故事嵌于社会动荡与变迁的大故事之中,增加了作品的张力和厚度。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