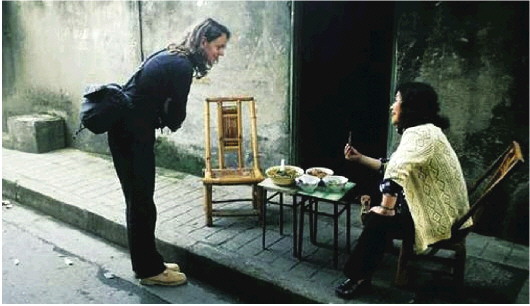食物触动味蕾,靠的是味道;逗弄唇齿,靠的是口感;抵达心肠,则归功于承载的情感。英国美食作家扶霞·邓洛普,因撰写中国美食而被人们认识。上世纪90年代,她来到四川成都,被朋友拉着去吃了人生中第一口川菜,从此与中餐结缘。继《鱼翅与花椒》《寻味东西》《鱼米之乡》等书后,最近她带来了新书《君幸食》。“总有人问我为什么来到中国,我回答:是为了吃。我并不是在开玩笑。从饮食中,我们足以了解中国。”新书分享会上,扶霞如是说。
□明生
走进中餐大门
1994年,四川大学迎来了来自剑桥大学的留学生扶霞。她最初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但显然,最终“引诱”她的,是中国的美食。扶霞花了超过十年的时间,研究中国美食和文化,甚至停留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家里的时间还要久,可见她对中国美食发自内心的热爱。
扶霞曾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还四次获得有“饮食世界奥斯卡”之称的詹姆斯·比尔德烹饪写作大奖,成为一名卓越的美食作家。《鱼翅与花椒》是扶霞最出名的作品,记录了她成为中餐美食家的经历。扶霞的热爱,不仅限于观察和品尝,更体现在她的亲身实践。她报名烹饪学校,学习四川方言,记录各种食材,全情投入练习刀工和烹饪技术,从剁肉、杀鱼,到剥核桃、腌制豆瓣酱,她找到了那个从小就在寻找的纯粹的世界,一个没有捷径、无法偷懒的世界。2018年,《鱼翅与花椒》被上海译文出版社译介出版,至今已畅销十余万册,斩获多个奖项。
2022年推出的《寻味东西》,收录了扶霞多篇发表于《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美食杂志》《洛杉矶时报》等知名媒体的随笔佳作。随笔分为四个主题,分别为“吃东吃西”“奇菜异味”“心胃相通”和“食之史”。扶霞用自己一贯的细腻与幽默笔触,生动描写了东西方饮食文化的各种差异和关于美食的精彩趣事:用不同材质的勺子能吃出不同味道的菜肴,宫保鸡丁、左宗棠鸡的由来,自己在伦敦家中后院亲手杀鸡吓坏邻居……在《寻味东西》中,扶霞侧重讲述东西方饮食艺术里的奇闻逸事,以及她面对这些差异是如何兼容的。
扶霞对中餐的热恋,后来又扩展至中国江南,这部分经历被记录在了《鱼米之乡》一书中。扶霞的江南之旅始于十余年前,第一站她去了历史悠久的美食之都扬州。和两百多年前的清朝皇帝一样,扶霞被柔软缱绻的温柔乡和灿烂美好的淮扬菜迷住了。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又数次下江南,遍访杭州、苏州、宁波和绍兴等古城,再返回现代化的上海。扶霞徜徉在古城的街巷通衢,造访路边摊和富商旧宅,流连于各式各样的后厨。她跟着当地的大厨与农民,出江河湖海捕鱼虾蟹贝,下村野田间挖笋和野菜,记录故事,学习菜肴,品尝人间至味。
在北至扬州、南至杭州、东至上海、西至南京的区域里,扶霞将多年来对江南饮食文化的观察与探索集结于《鱼米之乡》。从江南菜小史到当地人文风貌,从饮食习惯、烹饪特点到美食掌故,既拜访名师大厨,集结到诸多以往密而不传的珍馐佳肴,也流连于乡野田间,收录了民间朴实的农家菜和街头小吃。150余道经典食谱,108种常备配料,24种烹饪技法,精巧雅致、包容平和,传统精髓被不动声色地安放于饮食文化和历史之中。
站在西方人的视角看中国菜,能获得许多有趣的发现。扶霞在文中说,她发现镇江水晶肴肉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配点酱菜,美味无比;臭豆腐的味道就像法式蓝纹乳酪,嗜“臭”老饕不可错过;苔条鱼柳就是中国版的“炸鱼薯条”;腌笃鲜用意大利火腿制作也别有风味……
出海的中餐
扶霞新书名字挺有趣。“君幸食”即劝君进食、“吃好喝好”。两千多年前在狸猫纹漆盘内云纹间隙处朱书“君幸食”的汉代人,或许不会想到,未来会有外邦人以此冠书名,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写入日常饮食中。之前,扶霞的著作可以称为以饮食为主的“札记”,虽然也有学术方向的研究探索,但大大偏重趣味性的叙事。相比之下,《君幸食》有明确的研究构架和体系,试图从实践和文化两个方向来梳理中餐脉络。
这本书的故事,从糖醋肉球说起。“牛皮纸袋窸窣作响,我们将其打开,倒出里面的金黄色小球,都还冒着热气,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炸得酥脆的面糊包裹着软嫩的猪肉块,还配了个白色的一次性塑料杯,里面装满鲜红色的透明酱汁:糖醋酱。我和妹妹都兴奋得不行了。中餐外卖可是难得的享受,能在平时常吃的妈妈做的家常菜之外换换口味,还有机会玩玩筷子。摞在一起的铝箔碗盘,散发着酱油与姜的香气:这一套菜肴包括了虾仁杂碎、罐头笋炒鸡丁、粗砂砾状的豆芽炒面、面皮松软的卷饼(里面包的仍然是豆芽)、蛋炒饭。味道都很不错呢,但我们最喜欢的莫过于糖醋肉球,这是我们永远的最爱,怎么都吃不够。”她这样写道。
扶霞说,在上世纪70年代的英国长大的孩子们,很多人与中餐的初次相识,就是通过糖醋肉球。二战后,大批中国移民陆续接管了英国的炸鱼薯条店,逐渐在原有菜单上添加中式菜肴,中餐外卖店数量由此激增。这些外卖店的主打产品是借鉴和改良的粤菜大杂烩,其中包括豆芽炒面和杂碎,后者的英文名字也来自粤语,意思是“各种切碎的食材混杂在一起”。配料也很刻板:常见的去骨肉类轮番入菜,和罐头装的中餐常用竹笋、草菇、荸荠等以及新鲜的豆芽、洋葱和甜椒一起烹制,加上几种标准化的糖醋酱、番茄酱或咖喱酱,还有炒面或炒饭。
要让中国人来说,这些外卖根本算不上中餐。但在当时,食物都是定量配给,菜肴清淡无味,这些“中餐”如同来自远方的异国清风,“吹”到了英国。精彩多样的风味,不仅完全不同于土豆泥和裹面糊烤香肠,价格还很实惠。随后的几十年里,中餐成为英国日常生活中颇受重视的元素。到2001年,中餐已经成为英国人最喜爱的外国菜,65%的英国家庭拥有中式炒锅。
从特定视角看,中国菜在全球的崛起是个了不起的励志故事。这些主要由小企业家而非跨国公司推动的美食,没有其他任何同类的美食能产生如此非凡的影响或受到如此众多的喜爱,还能在如此数量的国家被接受并经历本地化过程。从纽约到巴格达,从斯德哥尔摩到内罗毕,从珀斯到利马,中餐在世界各地都形成了无法被忽视的文化。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典中餐”,从糖醋肉球到印度的“满洲鸡”、斯里兰卡的“牛油鱿鱼”和瑞典的“四小盘”。“中国菜”作为一个品牌,已经得到了全球性的认可。
不过,扶霞认为,换个角度看,中餐这种成功也反过来侵害到自身。经过简化、改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退化的粤菜,先是在北美发展起来,然后像五彩纸屑般在全世界遍地开花。但是,其菜式单一,涵盖的饮食范围十分有限,追求鲜艳的颜色、酸甜咸的重口味,油炸小吃和炒面当道,导致很多外国人对中餐形成不健康的刻板印象。
何谓中餐
几乎从第一次接触中餐开始,西方人对它的感情就很复杂,既热情,又犹疑。马可·波罗等一些早期踏足中国的西方游客对中餐的品质与多样性赞不绝口。不过,到了十八和十九世纪,西方冒险家对中国食物的评论变得越来越敌意深重。在中餐进入美国的早期,游客蜂拥至旧金山唐人街品尝异国风味。但“中国佬”本身对老鼠肉、蛇肉、猫肉和蜥蜴肉大快朵颐的事情,却成为大众文化的笑谈。
时至今日,偏见也从未完全消失。有数不清的人曾对扶霞使用这样的开场白:“你吃过最恶心的东西是什么?”脸上还带着打趣的笑。扶霞直言,长久以来,带有诋毁性质的、有关中餐的传说,一直是扩大种族偏见的渠道。有人利用这些传说,将中国人描绘成异类、危险分子、狡诈的骗子和尚未文明开化的野蛮人。即便是糖醋肉球这种历史悠久、伴随英美小孩童年的亲切菜肴,也常常难免被批判。
《君幸食》想要探索的问题是,何谓中餐,应该如何理解中餐,以及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如何吃中餐?这些问题都非同小可,不但涉及伦理与环境方面的一些重大困惑,也是一把钥匙,促使中国国门外的人从此开始欣赏灿烂的中国文化。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今时今日,这一点至关重要。同时,一旦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能帮助我们健康生活并纵情肆意地享受人生中最为深远的一种感官与智识乐趣。
在扶霞看来,儿时的那些糖醋肉球,无疑应该归属于中餐。它们讲述的故事,是中国移民想尽办法适应西方的新生活,创造出一种简单而经济的烹饪,既能养活自己和家人,又能迎合心存疑虑的西方人的胃口。这个故事里也有经济焦虑、地缘政治大事件与种族偏见的阵阵余波,这些元素的合谋,让西方人一叶障目,无法欣赏到真正的中餐。糖醋肉球同时还是一个鲜明辛辣的讽刺: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佐以酸甜咸酱料的廉价油炸中餐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偏爱,转头又将自己“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归咎于中国人。
近年来,中国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实力,以及中国移民群体在西方形象的不断变化,逐渐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菜的看法,中餐的地位有所提高。备受争议的“味觉仲裁者”《米其林指南》,也终于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餐厅,并逐渐将它们纳入国际美食家的走访版图。中国在进一步开放和更深地融入全球文化,势头看似不可阻挡。
然而扶霞指出,经济竞争和国际紧张局势有可能会阻碍这一进程。在此背景下,美食提供了建立联系和沟通的一种可能性,也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窗口。中餐,不仅是中国这个现代国家的食物,也是散居几乎全世界各地的华人的食物。“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既古老,也现代;既地方,也全球;既有着典型的中国韵致,也深刻地包容了多元的文化。中餐的工艺、理念、乐趣、智慧巧思和对养生的关注,都值得被奉为全球文化和文明的瑰宝。”扶霞表示。
(作者为书评人)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