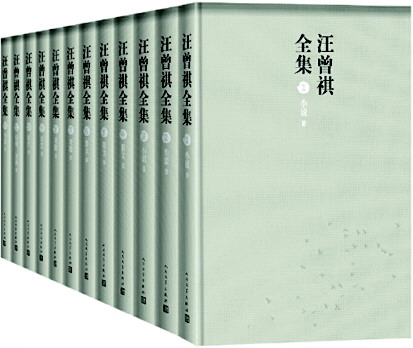古龙说,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心一窄想寻短见,就放他去菜市场。
汪曾祺大概是最爱菜市场的作家。“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他从市井烟火气里,嗅懂了人间值得。
转眼就是百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出版了。“鸡汤大师”也好,“最后一个士大夫”也罢,他只是喜欢文字。苦难能孕育辉煌,苦难能培养成熟,而他,是从苦难中学会了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随遇而安只是难安
在祖父的药店里撒娇,在父亲的画室中陶醉,尽情地欣赏着河里的渔舟、大淖的烟岚、戴车匠的车床、小锡匠的锤声、陈四的高跷……汪曾祺笔下,童年总是美好的。可这并不是他人生的底色,甚至也算不得是他人生的主流。
今年是汪曾祺100周年诞辰。风云激荡的这100年,注定了他肉体和灵魂的颠沛流离。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此时的汪曾祺正在江阴南菁中学读书。日本人攻占了江阴,江北也在危急之中。家乡高邮城再也呆不下去了,汪曾祺随家人到离城稍远的一个名叫庵赵庄的村子避难,一住就是半年。
后来,他把住的那座小庵,写进了小说《受戒》里。他的人生修行,又何尝不是从此时此地受戒的?
在庵赵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翻了一遍又一遍,冲着“沈从文”这个名字,他考进了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从江苏的家乡出发,先到上海,与同学会合后再由上海到香港,经越南才到昆明。战火纷飞,兵荒马乱,千里迢迢,怎么看这场求学之旅都难言轻松。
美丽的昆明翠湖、爱抽烟的闻一多、讲逻辑课没有逻辑的金岳霖、“男神”沈从文……甚至连“跑警报”,都被他写出了趣味。汪曾祺笔下,求学时光总是美好的。可是,联大生活只能算精神上的桃花源吧。
作为一个大学生,汪曾祺在昆明的日子真不轻松。穷的时候,甚至连一顿饭都吃不起。苦的时候,汪曾祺把自己的字典卖掉,换来食物果腹。房租也是经常交不起,幸好房东从来不催他。
成年人的世界里,哪有容易二字。何况是身处一个暴风骤雨的时代。
“中国各种运动,我是全经历过的。”进牛棚、写检查、游街、批斗、劳改,体验一项不少。
《随遇而安》里,汪曾祺回忆当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的过程,起猪圈、刨冻粪,扛着170斤的麻袋上“高跳”,往粮囤里头倒。他的长子、《多年父子成兄弟》里的主人公汪朗说:“这活儿我都知道,因为我也插过队,那都是苦活累活,那会儿他都是小四十的人了,能咬紧牙扛过来挺不容易的。”
汪朗记忆中,即便累成那样,父亲回来并不抱怨,而是“很兴奋,总是说个不停,向妈妈汇报他的劳动成绩”。他隐藏了自己的最深切的苦痛,在苦中作乐,只把快乐与人分享。
或许对年近不惑的汪曾祺来说,这苦不算什么,最苦的日子早已经历。
1946年的小品文《风景》中,初出茅庐受挫的汪曾祺,将自己称为“全像一根落在泥水里的鸡毛”。他写道:“我穷的不止是钱,我失去爱的阳光了。”那一刻,汪曾祺正经地想过自杀。所幸,他的灵魂导师沈从文给他关爱,帮他走出了阴霾。
1948年,他28岁,好像脱胎换骨了。落魄才子变身“鸡汤大师”,写下了一句话:“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有我这里一点是热的。”该是多么痛的领悟。
他的一生,和每个人一样,苦是实打实存在的。只是汪曾祺不太喜欢回忆痛苦,大概对他而言,这只会让自己更痛苦,别人读了也不会愉悦。
汪朗说,“老头儿”写过一首诗,前面四句是“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人间送小温,是他的作品,特别是60岁以后作品的一个底色,别人很难改变他。
有过走投无路,有过“心一窄想寻短见”,有过被人雪中送炭,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汪曾祺倾心于市井滋味,热衷于“人间送小温”了。
伤痕之外也有文学
汪曾祺是个“暖男”。在他看来,生活已经很辛苦,很累了,不妨“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不纠结、少俗虑,随遇而安,以一颗初心,安静地慢煮生活”。
只是,他口中的随遇而安,并不等同于逆来顺受。他的文章虽然充斥着饮食男女,但读起来并不让人觉得软绵绵。身可乱,心要安,这才是汪曾祺。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新收的一些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其中一篇是汪曾祺下放劳动时的检查,当时,他正在马铃薯工作站画图谱。
“我对现在的工作是有兴趣的,但觉得究竟不是我的专长……我总是希望能够再从事文学工作,不论是搞创作、搞古典,或民间文学,或搞戏曲,那样才能‘扬眉吐气’,问题即在于‘扬眉吐气’显然是从个人的名位利害出发,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对于‘立功赎罪’距离更远。”
他这检查还真是惊世骇俗,整个行文风格都不一样,跟写散文似的。汪朗笑称,这时候还想着文学创作,“真是志向不改,贬义词就是贼心不死”。
汪朗回忆,身处逆境,汪曾祺排解郁闷的方法,就是画画。汪曾祺写字画画,不暇研墨,只用墨汁。写完画完,也不洗砚盘色碟,连笔也不涮。下次再写,再画,加一点墨汁。
那段时间,他喝完酒铺开纸画画,画瞪着大眼睛的鱼,蜷着一条腿的鸟儿,画完以后还题字,上面写着“八大山人,无此霸悍”。温而不弱,他是借画画抒发自己心中的闷气。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作家忙于反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文坛蓬勃发展。汪曾祺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大家只在单一的词章、话语体系里写作,不可能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能探入人性的深处,当然也不可能把历史的和现实的东西交织起来加以立体观照,出不了曹雪芹这样的作家,出不了鲁迅这样的作家。
他认为语言的表达出现了问题。曾经受到很大创伤的汪曾祺很少直接地涉及反思题材,而是带着诗性、温馨的短篇小说重返文坛。
后来,许多人评价他的作品是“淡化”,淡化主题、淡化人物、淡化情节。汪曾祺不理解:“淡化,本来是浓的,不淡的,或应该是不淡的,硬把它化得淡了。”
在《七十书怀》里他解释,自己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那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说我淡化,无非是说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
但这就是由他的生活经历、文化素养、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你叫我怎么写?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
他并不隐瞒创伤。他写的《陈小手》,是很沉痛的。《城隍、土地、灶王爷》,也不是全无感慨。只是表面看来,写得比较平静,不那么激昂慷慨罢了。
何况选择“淡”的表达,一条“野路”走到黑而不畏批评,也是作家里有性格的了。
五四运动之后,文学的社会功用被渐渐放大,独自内省、深入个体盘诘的语体日稀。著名学者、作家孙郁说:“汪曾祺和他的老师沈从文都不喜欢过于载道的文字,趣味与心性的温润的表达,对他们而言意义是重大的。”
对本心的回归,就是他的“随心所欲”。如此看,汪曾祺是任性、固执的。
写爱与美并不可耻
汪曾祺是那个时代里大胆喊出爱的人。他觉得,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不是本事,不是能力,不是技术,不是商品,不是演出,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业余的,爱着。”
那篇石破天惊的《受戒》,在汪曾祺心底酝酿了几十年。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这样世俗题材的作品仍是需要勇气的。
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他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汪曾祺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他相信,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文艺有三种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和认识作用。汪曾祺不希望把美感作用和教育作用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把教育作用看得太狭窄。“那样就会导致题材的单调。美感作用同时也是一种教育作用。”
在他看来,美育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医治民族的创伤,提高青年品德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我们的青年应该生活得更充实,更优美,更高尚。我甚至相信,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
除了创作题材回归市井、关注“小确幸”以外,重新发现汉语之美,也是汪曾祺所努力追求的。
孙郁表示,汪曾祺的文字,一反左翼文学的那种腔调,把京派儒雅的、散淡的、趣味的话语结构召唤出来,把民国的话语整理召唤出来,重新衔接六朝文的趣味、唐宋文的美质、明清文的韵致。
这些恰恰是被新文化运动所颠覆的。汪曾祺对新文化运动、对胡适他们简单否定文言文的做法是有异议的。
他在国外有一次演讲,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背后是有文化的,胡适提出白话文,提出“八不主义”,他的“八不”,都是消极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没有积极的东西,要怎样?他忽略了一种东西,语言的艺术性。结果他的白话文成了‘大白话’。”
其实胡适词章里这些毛病,后来周作人等也都发现了。周作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也表示,文章的写作里面,不能轻易地否认文言的句式、文言之美。
汪曾祺的性格就像高邮湖的水,注定没法像鲁迅那样金刚怒目,他的骨子里是散文化的。所以,他一方面肯定文学是需要有战斗性的,需要有人去描写具有丰富人性的现代英雄,需要有人去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另一方面,他又在按部就班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他知道,那并不是他擅长的,而且已经有不少人写。
“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汪曾祺更愿意给人们书写一份快乐,送去一份爱。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