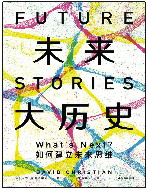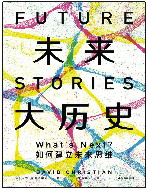
《未来大历史》
[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著
王恺昊 译
见识城邦|中信出版社
在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都在面临一个奇怪的生存奥秘,那就是未来。未来似乎有很多的可能性。然后,就在刹那间,除了一种可能之外的所有未来都消失不见了,留给我们的便是独一无二的现在。我们必须迅速处理好现在,因为它瞬间就会冻结成回忆和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在每一扇嘎吱作响的门后都有一大波其他的未来可能性在不耐烦地排队等待,队伍长得都望不到头。有的可能性平淡无奇,有的微不足道,有的神秘兮兮,而有的则能改天换地。我们不知道会碰上哪种。
这些关乎未来的奥秘令人着迷,但也很让人害怕。生命中的富饶、美丽、兴奋和意义——那些让人内心澎湃的时刻大多都是由这些奥秘带来的。我们真的想要知道每扇门后都是什么吗?两千年前,西塞罗曾发问:“元老院的议员大多是(尤利乌斯·恺撒)推选出来的,如果恺撒预见到了将要在元老院发生的……如果他预见自己将要被最高贵的公民们置于死地(而他们当中不少人的一切都是自己给的),如果他预见到自己的地位将会落得如此卑微,没有一个朋友——不,甚至没有一个奴隶愿意靠近自己的遗体,那么他该带着何其痛苦的灵魂度过一生?”西塞罗认识恺撒。在公元前44年3月的月中日(3月15日),西塞罗就可能在元老院目睹了恺撒被匕首行刺。恺撒死的时候,西塞罗正在创作自己关于占卜的伟大著作。所以,这个案例十分鲜活,也让人感同身受。生活中的戏剧性和兴奋感大多来自于对未来的无知,而这也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以及去深思熟虑的道德义务。
我们对于未来仅有的线索都来自于过去,这是最奇怪的一点。这解释了为什么生活会感觉像在一边盯着后视镜一边开赛车,也难怪我们有时候会撞车。在但丁的《炼狱篇》里,作为惩罚,占卜者们的头被扭向了后方。和他们一样,我们也是在回望过去时步入了未来。所以,当花费大量时间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们却很少思考未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讽刺。《未来大历史》的目的之一在于构建一个过去思维(也就是“历史”)与未来思维的连接案例,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用过去照亮可能的未来。
通过“大历史”的不同镜像,这本书探寻的是我们对于可能的未来会有哪些思考方式。“大历史”,这一方兴未艾的跨学科领域也正是过去三十年我教学和写作的母题。大历史会用所有可能的维度和不同的学科视角去看待过去。大历史还相信,用类似三角测量的方法会产生对于历史更丰富、更深入的理解。大卫·休谟曾说自己在“深究”难题的过程中找到了乐趣。我也希望大历史的视角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未来。
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这是种很有力的办法。跨界学者创造了现代科学的基本范式。比如,大爆炸宇宙论把关于至大与至小的物理连接了起来,现代遗传学则是结合了化学、生物和物理。就像丝绸之路那样,大历史的视角可以把很多知识领域如纺线那样交织在一起,并由此创造出新的见解和思维方式。在如同未来思维这样困难重重而又支离破碎的领域中,打造新的联结会格外重要。温德尔·贝尔可谓是现代“未来研究”领域的先驱之一。他曾写道:“在这个不乏专家和专业知识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他们有大局观,看得懂不同事物如何相关关联,能看得到整体而不仅仅是一些局部。这样的人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是当下他们被忽视了。”
与穿行于丝绸之路一样,跨学科当然也很冒险。多视角的观察也偶尔会在细小之处、微妙变化或者精确度方面略打折扣,而我希望能让两者得到平衡。在《生命是什么?》一书的序言中,量子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把这一困境说得很清楚。在这本跨学科著作的启发下,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在DNA领域的见地也很具有突破性。薛定谔明白自己并非研究生物出身,但他很清楚物理学可以给生物学提供很多帮助。他写道:
想要摆脱这种困境(把多个学科的观念连接在一起的困难),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出路……除非我们当中有人带着二手素材和一知半解就去冒险。他们冒险涉足跨越实证和理论的综合性研究,而弄不好就会洋相尽出。
说到探索未来,本书秉持的也是相类似的精神。它想让我们“深究”对未来的理解。然而,它也想为此“广泛涉猎”,想从许许多多不同的方面去接近未来,尽管这似乎有点自相矛盾。本书将会探索以下几个问题:为了理解未来,我们做了哪些努力;我们和其他生命体如何管理不同的未来;我们人类如何为最可能发生的未来做好准备;最后,在人类的想象中,我们自身的未来、我们地球的未来乃至整个宇宙的未来又都是什么样子的。
(本文为《未来大历史》序言,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