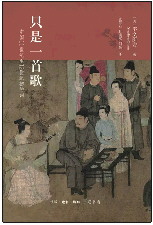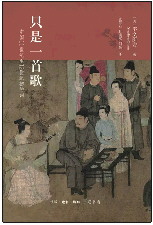
《只是一首歌:
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
[美]宇文所安 著
麦慧君 杜婓然 刘晨 译
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
女性在早期的词作中绝对占有中心的位置。不仅因为她们的爱与被爱是词的主题,女性也在词的实际表演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苏轼的词集中有不少写给歌女或有关歌女的作品。它们听上去不像传统的小令,但用了一些传统小令的套语。这部分作品很少出现在现在的词选中,也很少被评论家们关注——除非它们离苏轼的风格太远,致使评论家们质疑其真伪。人们或许会认为这部分作品不被重视,是因为它们不符合苏轼作为“豪放”派词宗的形象;但它们之所以重要,正是其中所体现的苏轼的机巧和才思。
“严肃”的词作或许容不下任何女性,但她们却在苏轼最广为流传的杰作中回归了。只不过,这些归来的女性要么已身故多年,要么身在远方,要么是纯粹虚构的人物。尽管苏轼绝非无情之人,却总是对情感有所拒斥;而且似乎不堪承受词的论述体系中的情与逝。
苏轼最动人的词作莫过于《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这首词作于1075年,记录了苏轼梦见亡妻的情形: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似乎想不带伤感地传达情感——这并不容易。副题中并没有点明他梦见的对象,因此上阕也可以解读为他对某个故去的男性友人或家人的怀念。但或许最奇怪的还是他提醒读者自己“不思量”:他无意忆旧,但回忆不期而至。词中虽然明确说了他“无处话凄凉”,但根据上下文,“话凄凉”的主语也可以指他亡妻的魂灵。他最后一个保持疏离的举措,是说她应该已经认不出今日的自己了。但苏轼越是要保持距离,他所传达的情感就越是深厚真切。
怀念亡妻和梦忆故去的家人是适合入诗的主题。反过来说,这并不适合写成词作。这种主题不但和表演不搭调,且完全无法在需要唱词的社交场合表演。我们不知道苏轼为什么选择填词,但可以猜想,词的传统似乎是唯一可以让苏轼处理自己的感受和感伤的方法。而一旦苏轼写了这样的作品,“悼亡词”(多半是追悼亡妻)便开始在他的圈子中出现。
苏轼常常自称“多情”。这个词最好的翻译大概是“易受强烈情绪感染的”(suspectibleto strong feeling)。根据上下文的不同,“情”有时表示“感伤”,有时表示“热情”。苏轼在《赤壁怀古》中用“多情”一词形容自己,原意是说他这种性情应该会被人笑话。就某种意义而言,苏轼或许是“多情”的,但他总是在竭力抵御这种“多情”,尝试在自我和其关注的对象间制造障碍。这些障碍一般是诙谐怪诞的反讽,但至少有一次是实在的一堵“墙”,即下面这首小令《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恼”,此处译作“烦乱”(agitated),有时候也可译为“困扰”(bothered),但这也可以用来表示欲望的影响,尤其表示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当然,墙内的少女并不“无情”,只是她不知道自己的笑声对一个过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看不到她,只能从她的笑声推知这是一位“佳人”。苏轼作词时一贯热衷于把自己置于中心,此处却令人惊异地隐身了。如果词中之人是“多情”的,那么写词的人则刻意置身事外,从一定的距离观察整个场景。
对苏轼而言,这或许就是词的核心任务:他不像道学家那样试图压抑人心的起伏摇荡,他接受这种摆荡,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思量它、美化它,并报之以微笑。其他的词人也努力用语言捕捉这种人心的起伏,却鲜有成功者。
词的传统从本质上是对11世纪中后期日益严苛的宋代公共价值的歧出与反拨。词颂扬情爱,视之为生命中唯一可宝贵之物,这与其他许多居于中心地位的重要诉求背道而驰。那些诉求强势而多样,从新生的道学到社会分层,再到致力解决国家的问题都有。和之前的隐逸传统类似,主情说也正是靠了反抗和拒斥那些经世诉求才获得力量的。有些人参与了“主情”的讨论;有些人则如贺铸一样,亲身实践了“主情”的生活。而苏轼却游离在所有群体之外:他无法接受道学家对人类自然响应世界方式的无视无知;他不只想要进步;王安石的新党试图将国家看做集权管理的工具,并从这个机制理解人类社会,而在他们失败之后苏轼却也不能苟同继之而来的现状;他同样无法靠传统意义上的词来拒斥一切其他的价值,因为他并不相信男女之情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无论是标准的社会角色,还是歧出的新角色,苏轼都不厕身其间。大部分人爱这样的苏轼,但间或也有人恨这样的苏轼。他有种天生的直觉,能在所有新旧角色之外找到一个有趣的立身姿态。
苏轼词中写到许多女性都曾为他倾心,但他不是晏几道。苏轼对女性最有魅力的时候大概是在家庭生活中。他的词中没出现过被叫出来在友人面前表演的姬妾,但他的词里有惠州的朝云。朝云侍奉他多年,一路跟随他来到广东惠州的贬所。这是苏轼词中没有“缺席”的一位女性。但她也将在惠州死去。
朝云不像晏几道的恋人那样深深焊入他的记忆,她是惨淡生活中的一种恩赐。苏轼是维摩居士,朝云则是天女,在他家徒四壁的屋里撒下花雨。苏轼晚年写给朝云的这首《殢人娇》是另外一种情词,恰可与晏几道最好的那些作品构成绝佳的对照: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菜。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好事心肠,着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这和苏轼那些豪放的名篇有很不一样的基调。苏轼还有两首《浣溪沙》词似乎也是写给朝云的。很显然,朝云这里问苏轼寻的一首好“诗”,其实就是他的“词”。
(摘选自《只是一首歌: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