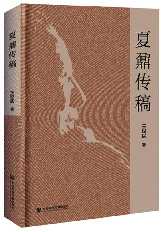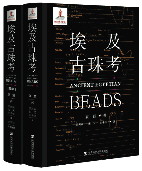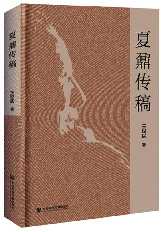
《夏鼐传稿》
王世民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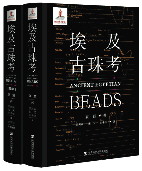
《埃及古珠考》
夏鼐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世民在夏鼐身边学习、工作30余年,先后整理了400万字的《夏鼐日记》、增订了220万字的《夏鼐文集》。在近20年的积累上,所著《夏鼐传稿》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成为夏鼐的第一部人物传记。
□鹊华秋
清华园里读书忙
上世纪30年代,清华园里有两个学生爱写日记并流传至今,一个是季羡林,另一个是夏鼐,两人均为清华大学1934届毕业生。
1931年,教育家梅贻琦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12月3日正式到任,并向全校师生发表讲话,提出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
当时正值清华大学早期的黄金时代,图书仪器完备,各科名师云集。清华园读书风气很浓,老师对读书的要求也很严,给学生布置了大量阅读材料。即便是节假日,清华大学图书馆也座无虚席。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夏鼐尽情地享受着阅读的乐趣。
纵观他在清华期间的日记,记事大都很简略,而“读书账”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很多时候,日记的内容就是当日读了什么书、读了多少页,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比如,1931年10月4日至8日的日记,只记了“阅书:《莎氏乐府本事》(全书368页,完)”这么一句。10月12日和13日,同样也只有一句“阅书: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全书290页,完)”。由此可见,读书几乎填满了夏鼐清华生活的全部。
1932年初,夏鼐在日记中计划,本年预备课外读50部以上100部以下的书籍;法文至少要认识2000个以上的生字(单词),年终时能够翻字典阅读浅近的法文书。暑假中读点外交史的书,同时对中国通史方面已出版的书籍,加以系统的研究。
实际上,日记翻到9月9日,他的阅读量已达50部。这一年里,夏鼐共读书66部,超额完成任务。1934年1月1日,夏鼐写道:“今天是元旦,但是佳节良辰对于我已失去它们的意义。我仍是依着预定的计划,读了一卷《通鉴纪事本末》。”在《夏鼐日记》中,屡屡可见他自我督促阅读进展的记录,如“此书颇欲从速阅毕,今日起非赶快阅读不可”等,从中皆可体会夏鼐渴望多读书、快读书的迫切心情。
《夏鼐传稿》中提到,为学好钱穆的“战国秦汉史”课程,夏鼐从上年年末开始,认真阅读《史记》及三家注,并参考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对《六国年表》《魏世家》《秦始皇本纪》等进行校订,先后写成并发表《魏文侯一朝的政治与学术》《秦代官制考》二文。
夏鼐在清华大学所学专业为中国近代史。据《夏鼐日记》所载,夏鼐所读书中专业书占了一大部分。不过,夏鼐的阅读视野没有限于史学一隅。相反,他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读了大量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还把触角探到文学领域,读了一批中外文学名著,如鲁迅的《伪自由书》、茅盾的《子夜》、伏尔泰的《老实人》、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
埃及学第一人
1935年,夏鼐留学英国,转攻考古学。1946年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位埃及考古学专家。
选择埃及学,夏鼐经过了深思熟虑。在英国,他一开始进入的是爱丁堡大学,这里只能学习史前考古学,无法学习国内最缺乏的历史时期考古学。夏鼐感到,抵达英国以后,在田野工作的技术方面已经用力不少,短缺的主要是“发掘后如何整理、采集标本后如何研究”方面的知识。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绝非仅仅听讲即可掌握,“必须有具体之实物及实例,始能领悟,然后始能以其方法,返国后应用于搜集及整理中国之古物”。
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与埃及息息相关。基于此,他进一步认为:“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故中国之考古学界,必须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学,以其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镜。”因此,决意转入埃及考古学系。
当然,其中的困难是巨大的:需要花时间学习艰深的古埃及文字,需要注重发掘及保存古物的科学技术,需要广泛阅览参考书。不过,夏鼐最终都一一克服。
在求学期间,夏鼐有机会两次实地探访埃及,并参与考古发掘研究。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著名的《埃及古珠考》。串珠在埃及考古里是一种常见的文物,一具木乃伊往往随葬成千上万颗珠子,在这个领域,夏鼐的成果至今无人超越。
夏鼐埃及学综合实力究竟是个什么水平?《夏鼐传稿》讲了一个小故事。1956年和1957年,根据中埃文化合作协定,中国科学院先后邀请两位埃及历史考古学家费克里和埃米尔·埃芬迪,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埃及古代史”和“埃及考古学”两门课程。
讲课时,往往由夏鼐将讲稿译成中文,或亲自担任口译。有一次,某专家面对提问讲不清楚埃及古代史上的某个问题,还是夏鼐进行补充才得解围,将问题说清楚。
这位专家结束讲课时尴尬地表示,自己讲的这些事情,夏先生都熟悉,而夏训先生熟悉的许多事情,有的自己却不大清楚,今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就近向夏先生请教。
定陵发掘的背后
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田野考古发掘,肇始于上世纪20年代。考古学是外来学科,老一辈考古学家中,除李济在国外主修人类学专业、接触过田野考古外,真正在国外经受过科班考古训练的只有三位:梁思永,卧病十多年,身体极度虚弱;吴金鼎,于1948年9月去世;再一位就是夏鼐。
正如《夏鼐传稿》所说,新中国成立时,夏鼐是大陆唯一既在国外受过正规科班训练,又有丰富实践经验和重要贡献,并且能够亲临第一线的田野考古学家。因此,无论是建立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培养田野考古骨干人才,还是主持考古发掘、开展考古研究,都绕不开夏鼐。
夏鼐一生考古成果颇丰,这里只谈争议最大的明定陵发掘。1955年10月,吴晗联络郭沫若、范文澜、沈雁冰、邓拓、张苏五位知名人士,上书国务院,请求发掘北京明十三陵中永乐帝的长陵。郑振铎和夏鼐坚决反对,夏鼐亲自劝说过吴晗,不要急于搞这项发掘。
不过,国家还是批复了计划。夏鼐作为中国田野考古方面的权威人士和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顺理成章地负责具体的业务指导,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重担。
长陵居十三陵之首,规模宏大,地下结构复杂。夏鼐认为,不宜贸然行事,应先选择规模较小的其他陵墓试掘,取得经验以后,再考虑发掘长陵。
从1956年5月破土开挖,到1958年7月墓室清理结束,定陵发掘工作历时两年零两个月。这段时间,《夏鼐传稿》作者王世民正在夏鼐身边的考古所学术秘书室工作,深知夏鼐为定陵发掘的操劳情况。
王世民回忆,那时,夏鼐身患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饮食稍有不适便会接连呕吐。发掘的每个关键时刻,都需要夏鼐亲临现场进行具体指导,所以王世民不时接到工地打来的电话。一般情况下,夏鼐都是第二天一早就驱车前往。由于定陵工地生活条件较差,夏鼐往往停留一两天就因呕吐不止而折返,稍事恢复再重新前往。
夏鼐要求在发掘中分头做好文字记录,因为稍有疏忽,便会给后来的研究工作带来困难。当时每天的记录文字甚多,有时不下万言,都会请夏鼐过目。每当深夜,发掘队人员结束工作后,夏鼐经常通宵达旦审阅记录材料。
王世民透露,1957年9月地下玄宫打开后,夏鼐在定陵坐镇十多天。当时,首倡定陵发掘的吴晗,热衷于接待各方领导参观,对发掘工作记录情况并不上心。甚至开工两年间,竟未测绘过发掘坑位图,夏鼐屡次催促未果,不得不亲自动手补测。
1958年5月清理万历帝后棺内文物期间,是夏鼐在定陵发掘中最辛劳的日子。潮湿、黑暗的地宫内,大家工作紧张,夜以继日。夏鼐拖着病体,和青年人一起,不分昼夜忘我工作,历时两周。
1958年6月下旬,定陵地宫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夏鼐却完全病倒,先住进北京人民医院,再转往小汤山疗养院,疗养了五个月。这是他生前疗养时间最长的一次。
定陵的发掘,使夏鼐及文化部有关领导更深切感到发掘帝陵的条件很不成熟。于是以文化部名义上书国务院,提出:“在帝王陵墓中很可能有较多的随葬品,但是目前有些文物的保护技术问题还没有解决,如彩色漆木器、竹器等易变形,丝绸、纸质类等纤维材料的科学保存等。在这种科学技术问题尚未解决以前,如果不进行发掘,暂时保存在地下,当不会破坏,一旦发掘出来保护不好,反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他们主张古代帝王陵墓,除配合基建必须发掘外,最好暂时不作主动发掘。
国务院随后明确:“目前考古发掘工作应当以配合各项建设工程为中心任务,凡不属于配合建设规划或工程范围内的帝王陵墓及其他发掘工作可暂缓进行。”因此,长陵的发掘就此作罢。某省跃跃欲试,一再试图主动发掘本省帝陵的打算,也成为泡影。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