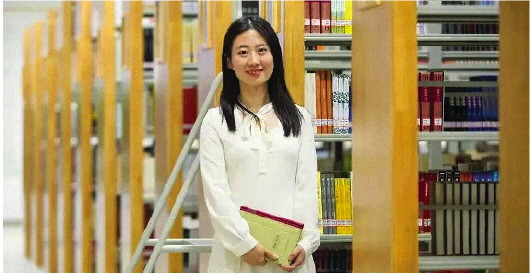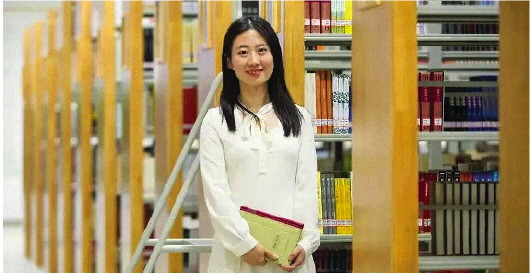
筹建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的杨素秋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杨素秋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八十本书环游地球》
[美]大卫·丹穆若什 著
宋明炜 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
章瑾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祁宇
书单推倒重来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本书记录了杨素秋于2020年9月到2021年9月,在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挂职的经历。作为副局长,她负责文化科、文化馆、旅游科和规划中的图书馆,该书就重点记录了碑林区图书馆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
当地策划了一个大型文化综合体,体育馆、文化馆、档案馆、图书馆各一层,其中图书馆占地一万多平方米,但是建设需要时间。当地找了一个现成场地做临时过渡图书馆,采购图书书目的事,原本应该是图书馆宁馆长考虑,但馆长把这事全权委托给了杨素秋。
杨素秋凭借着自己对公共图书馆的理解,一点一点搭建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图书馆。比如,碑林区是市中心商业繁华区,周末常有家长带小孩子来附近逛街,要增加文学书和少儿书;离图书馆步行只有几分钟的地方有全国最大的石碑博物馆,展出的不是绘画或者器皿珠宝,而是“字”,应该设立一个碑帖专区,做成特色;在碑林区工作的外国人不少,可以设立一个单独的外文童书区;应该有一个漫画专区,还要增加盲文书。
建设图书馆的公告刚刚在政府网站发布,杨素秋就陆续收到了各方推介的书单。大量情感鸡汤书籍和长篇小说,书名软糯可人,其共同特征是书评网站查无此书。偶有经典作家,恰恰剔除成名作;偶有经典作品,恰恰绕开优质出版社。儿童书籍则完全杜绝国际大奖和畅销绘本。还有一些“单蹦”的图书,第2辑,第5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另有一些诸如报告《某某县政府廉洁反腐败的公众感知评估报告》、学术著作《主体间性视野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
“书店里卖不动的书、仓库里的滞销书以及那些明知没有读者的自费出版书籍,全都塞给了我。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某些图书馆书架被三流书籍占满。”杨素秋直言,因为图书馆是公益场所,不赚钱,塞些“坏”书进来不影响图书馆“业绩”,反而会增加书商利润,于是,图书馆成为某些书商的库存倾销处。
“我无法想象我一手弄起来的书架摆的全是三流书,走在里面多丧气。图书馆不能只做成政绩工程,为了读者喜爱,我得把好第一关。”这座图书馆馆藏需要8万册书,经过各种考量,杨素秋和宁馆长决定第一年的100万元买书经费一共选1万种图书,每本3本副本。剩余的书,等到第二年经费下来再补充。
要找到近年出版的1万种较受读者欢迎的书,并没有现成路径。杨素秋一头扎进书目的海洋,豆瓣各类别图书top100清单,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月度年度榜单,购书网站实时销售清单等,都被她一一输入表格研究。
6个月后,图书馆顺利开馆。开馆前,杨素秋在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花了半年时间,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座不网红的图书馆》。一座区图书馆的建立,就这样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也有了这本书出版的契机。
众口难调也得调
2021年度买书资金到位后,馆长再次把书目之事委托给杨素秋。
“第一年编的书目,我凭主观推测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诉求,而建馆后与读者的交谈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人们兴趣差异之大,让我感到自身的匮乏。”杨素秋不看“鸡汤”,但运营的图书馆会有“鸡汤”,而且是她精挑细选的“鸡汤”,就是在“鸡汤”里面找那些“熬得比较好”的。
杨素秋的观点是,图书馆里还是需要这类书的。图书馆是纳税人的钱建的,如果纳税人很想看这类书,给不给他买?如果“鸡汤”确实能够给一部分人提供及时的抚慰呢?杨素秋自己也承认,曾经在18岁的时候被“鸡汤”抚慰过。
杨素秋意识到,读书是一个拾级而上的过程。有的人读成功学,他会觉得这些书虽然看起来特别“鸡血”,但是对他创业就是有一些帮助。“那你让不让他读,或者你要不要给这类读者提供这方面的书?我的观点是要的,要尽可能照顾到各种群众的需求。”
为了一份更好的书单,她在手机通讯录里寻找,挑几位精通专业的爱书市民,再挑几位普通的爱书市民,还要兼顾高龄读者和年轻人,前前后后一共50多位亲朋好友为她出谋划策。为了不占用朋友们太多时间,她只需要三项:书名、作者、出版社,其余数据,例如ISBN号、定价、出版年份,太琐碎了,就自己来做。
什么样的书不选呢?就是那种又偏门又“烂”的书。“我们知道有一些书很小众,但它们是精品;但有些又偏门又烂的书,比如说某某校报文化副刊选集,一看就是书商拿来蒙我的,这样的书我们坚决不进,这是当时我选书的原则。”
这一标准来自于她的经验。杨素秋去过非常偏远的山区支教,也去过一些农村图书室做调研。一些农村有图书室,却被锁起来。她问管理者为什么锁起来?管理者说,因为没人看。杨素秋进去一看,都是《化肥的使用方法》《淡水鱼的养殖要点》。杨素秋直言,不管是面向农村的小孩还是成年的农民,可能都不想看这些书。高校的农业、畜牧业专家也许更想看这些书,农民更需要的是手把手教他。买这些书也是花了很多钱的,之所以束之高阁、被锁起来,就是因为买书的人不知道人的需求。“这两年,我更愿意做一些公益活动,到偏远的地方,不管是捐书,还是做公益活动,总是想改变一点点,我也希望政府层面能够推动这件事。”杨素秋说。
建设碑林区图书馆的时候,考核标准里有面积,还有书籍的数量,即根据这个区的人口核定出来的最低数量,不能低于多少本。杨素秋觉得,当用面积、数量考察一座图书馆合不合格的时候,这实际上是量化的方法。至于这座图书馆的藏书好不好、有没有满足当地民众的需求,是特别难考核的。
杨素秋认为,还是可以想一些办法。“如果将来我们农村的图书室里不再都是《化肥的使用方法》这类书,才会让小孩子在大人们下地干活、外出打工的时候,不只是刷抖音、快手;如果离他们家5分钟路程的农村阅览室里,有大量的绘本、立体书,我觉得对于整体民众阅读氛围的培养是很有好处的。”
杨素秋直言,自己小时候看特别多的“闲书”,也没有觉得影响学习。有了亲身体验,杨素秋在碑林区图书馆的童书选择中采用了更接地气的方式。“我在建馆过程中会特别注意9岁至18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他们想要阅读什么样的书。很多家长知道要给孩子看绘本,但是从孩子相对比较幼稚的阅读到成人阅读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观察来到碑林区图书馆的初中生,通常家长会给他弄一堆卷子在那儿做,然后家长玩着手机,看着他做。那些学生很痛苦,如坐针毡,有时候偷偷去拿一本漫画,他的父母就会说,这个不可以的,你去借一本作文书。”
杨素秋会刻意地给这个年龄段的小孩选很多科普书、历史书。她希望能够让家长跟孩子一起有一个意识上的转变,不是说刷题就一定能变成未来的成功人士,没有这样的公式。
打破认知的局限
做公共文化的过程,一次又一次让杨素秋意识到,不管一个人多么地想要消解自己的偏见、想要打开自己,还是常常处于职业认知所带来的局限当中。
有很多读者问她,已经有这么多的电子书,从网上买书也很方便,现在很少去图书馆,为什么还需要图书馆?杨素秋认为,社会在阅读方面的确正在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往往会从自我出发去想象这个社会的全貌。
杨素秋走访过的低收入家庭里,很多没有书架。这些家庭的孩子除了免费的义务教材以外,顶多有那么一两本作文书、教辅书。在她看来,这不怪家长,因为这些家长没有财力、精力或者相应的知识结构为孩子挑选适合的书。每次走进这样的家庭,杨素秋不会居高临下地“哀叹”这些家长为什么不为孩子挑选好书。“那些家长可能挑选蔬菜或者别的什么能力比我强多了。我只不过恰好在这个职位上,更擅长帮小朋友挑书而已。这种情况下,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就这样无奈陷入了短视频或游戏的旋涡,因为他的生活中没有低价或免费的优质文化产品供他去选择。如果你的周围都是跟你同阶层、同收入的人群,那你很可能就看不见这些人。”
挂职前,杨素秋认识一两位盲人朋友。因为要建设图书馆,她接触了更多的盲人。杨素秋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对他们的“想象”是非常刻板的。
杨素秋第一次采购盲文书时候没有经验,根据盲文出版社提供的书单来采购,大部分书籍是讲按摩技巧、理疗、中医经络的,还有一些关于乐器演奏的,文学、历史配得不多。当时,她想象出来的盲人需求就是这样。
结果盲人朋友来了以后,最想摸的书是世界地图集。杨素秋问为什么,盲人朋友说:“我这辈子一直没想清楚经线和纬线是什么。”后来,盲人朋友告诉杨素秋:“你不要认为盲人跟你们完全是两类人,我们跟你们也一样,我们也爱读文学和历史。我现在特别想读《三体》,你能帮我买一本吗?”
杨素秋希望大家能突破自我群体的局限性去倾听他人的声音。“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想表达,听不见别人的声音,尤其听不到别人的异见;我们很喜欢别人给我们点赞,因为点赞就是赞同,哲学家韩炳哲说点赞是一种最浅薄的经验,但我们痴迷于无数的点赞,对于跟我们的观点相差很大的意见,选择‘我不听我不听’,把自己关在一个信息茧房里,这是需要去反省的。”
(作者为书评人,供职于基层文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