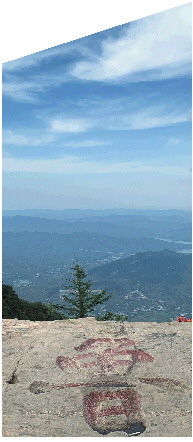□蔡哲宇(山东大学文学院2019级毕业生)
离开山东时,我选择了最慢的一趟火车。火车慢慢地经过北园,把济南交错的立交桥和电动车大军落在窗外;随着远处泰山山脉的连绵起伏,一个个熟悉的地方渐渐被抛在了身后。泰安之后是兖州,金口坝一晃而过,李白在这里写下“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空宜”。接着是济宁任城,我和放学不愿回家的初三小朋友打了一场傍晚的篮球赛。最后是菏泽,我就着卷饼喝了碗羊汤,然后在公园的牡丹亭听大爷和小徒弟拉二胡,临走时大爷说我会成为一名好记者。
一切都已经过去,夕阳把一闪而过的电线杆拉得很长。光线逐渐暗淡,于是我又往窗外看了一眼,这次只看到了玻璃中的自己。
古迹并不一定是亭台楼阁,更多时候往往只是遗址,甚至是一抔黄土、一块立碑。我去临淄正是初春,土地尚未播种,荒黄了无生机,光秃秃的杨树枝凌乱地交叉在一起,几个搭起的鸟窝格外显眼。两千年前,这里曾是齐国的都城,来往的行人摩肩接踵。如今,只有北边一处坑洼里的叠砖和一小座夯土无言地诉说着消逝的恢弘。我裹着羽绒服,溜达着测算齐都北门到南门的距离——大概五十分钟路程。在城垣遗址的不远处,坐落着齐国大臣晏婴的坟墓。墓堆上杂草丛生,五十米的甬道就嵌在农田之中。不远处有几个农民正侍弄着田地,阡陌之中立着几块小土堆,斜插着的白幡随风飞扬。
风景并不只在目的地,沿途也有风光。有一次我和同伴在兖州寻找杜甫作诗的少陵台,正当春末午后,路遥人困,于是随处找了块榉树下的石板,把背包枕在脑后,席地而躺。朦胧恍惚之间,微风拂过树梢沙沙作响,叶片轻轻摆动摇晃,阳光从缝隙中泄漏,点点洒在身上。起身又行数百米,李白醉卧的酒仙桥正安静地横跨在一条小溪上,不远处有个小卖部,我们买了一瓶二锅头,往桥面洒下一半,看着酒滴融入溪水流向远方,然后又各自抿了一大口,辣得龇牙咧嘴。那一刻,相顾间的大笑就是我们此刻最重要的事情。
从这之后,我很少再为行程做规划。
在山东的四年里,我虽然生活在其中,有时又像个局外人好奇地观察着一切;但在大学校园里,我常感受到某种断裂与脱节。这一方面源于我所学的古代文学专业,如果只是背书考试,如何能真正体会那些在生活中书写、在生命中实践的诗篇?另一方面,图书馆里的小书只教给人理论上的“应然”,可当面对社会的种种“实然”,不免让人感到困惑。沈从文在《从文自传》里说:“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对此,他自称为“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因而除了游山玩水,我也决定在山东这本大书里寻找答案。
在滨州,社区略显孤独地矗立在一望无际的平野上。通过居民的讲述,我听到了政策愿景与落地实施的差距,听到了各方利益冲突与博弈的过程,从中理解着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在荣成成山,本是被尖顶的海草房所吸引,却意外被“情报组”的老太太们拉着坐在马扎上,一边陪着掐韭菜,一边听她们絮叨村子里的白事、新鲜事,然后是陈芝麻烂谷子事。渐渐地,我也从她们口中听到了对于乡村振兴的真正期待。在文登的一个宗祠里,我遇到了正校对族谱的大叔。在他自豪的话语间,我也琢磨着当今与明清实体性宗族、中古观念性宗族的异同。事实上,我和他们的交谈多是只言片语,许多观察也只停留于浮光掠影,但我的好奇心得以安放。尽管模糊甚至仍无答案,我也可以自由地遐想历史和当下,思量理想和现实。
理解也是一种愉悦。和不同的人产生交集,让我真正感到和这片土地有了连结。
有一次,我和同伴倒了两趟火车再转了一辆班车又步行三公里,只为一睹武梁祠的真容。这座建于东汉的武氏家族墓群石刻,安静地坐落在嘉祥纸坊镇的武翟山村,雕刻着代表儒家艺术的画像。然而面对紧闭的大门才得知,由于文物保护修缮,这里已经关闭了很长一段时间(由此可见,适当的规划也还是必要的)。看着不动如山的门房王大爷,我们一左一右地求情道:“转了两趟火车,又在县里坐班车,最后从镇子上走来的!你们这也太远了吧!”“我们是山东大学的,绝对不乱动。”“您行行好,就让我们看一眼吧。”大爷到底还是心软了,把手摸向了腰间的钥匙:“低头跟着我走,问起来就说是王大爷孙女的朋友。她在山东师范读书——别露馅了。”
吱呀呀门打开一条缝隙,省文保队的工作人员正在院内穿梭。一间侧屋里,一个人正眯着眼睛看电脑上的数字,另一个正甩着蓝色的试管摇头晃脑。大爷把我们带到了里边的库房,板着脸背着手一一介绍,自豪之情却溢于言表。一块块青石静立,位于屋顶的祥瑞代表天界的意志,山墙的西王母、东王公则象征仙界,磨损的石面闪烁着岁月的光泽。墙壁则讲述人间,如古书的顺序描绘短裳的三皇、冕冠长袍的五帝;伏羲黄帝则撇头向后,像在引导后来帝王;紧接着出场的是守节烈女、伏泣孝子与贤臣名相,一一把历史、道德以及政治标准具体化;核心部分是一座双阙主厅,阁楼顶部有凤凰、猴子和有翼仙人,旁边杵着一棵连理树,中间端坐着一位君王,身后站立着手持笏善的侍者。武梁位于最末,满心期待这座祠堂成为“后世凯式,以正抚纲”,可惜其身死不久便在战火中轰然倒塌,随后被掩埋在历史的黄沙中,待到重新为人发现时,石缝中已经探出了油油的青草。
我们不知道站了多久,只是呆呆地凝望着,几声清脆的鸟鸣才把我们从现实中唤醒。恍然迈出大门,大爷又追了上来,还是板着脸:“刚才俺给你们找辆三轮送到镇上去,已经谈好了。”于是我们爬上三轮敞着的后厢,挨着一捆秸秆坐下,眯着眼睛抵挡被风吹起的浮土,一摇一晃地告别了王大爷。
如果恰好遇上饭点,就更有几率蹭上一顿饭。在枣庄的火车上,只因为香气多瞟了几眼,对面大哥就慷慨地递上了一双筷子。经过几轮言不由衷的推辞,我开心地接过饼,卷上葱,再夹上袋子里装的豆角炒肉,当起了大哥军旅生涯的听众。在临沂,我坐在石凳上托着下巴发呆,一位大妈正用石碾来回把黄豆、小米推轧成粉,言语之间发现大女儿竟然与我是校友,于是欣然邀请我去家里尝尝鲁南特色粥和烙饼。
在滕州北关,我在午间偶然走进一处教堂,一位姓汪的大姨同样热络地为我添上筷子,端上一碗萝卜烧肉、一盘韭菜炒蛋和一盘馒头。在餐前祷告过后,几位牧师七嘴八舌地介绍着滕州的各个角落。下午,他们又推举出一位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牧师,开车带我逛遍了老县衙、博物馆、龙泉塔和麻风病院旧址。他在请我品尝地道的菜煎饼后,又给我拎了两根玉米路上吃。秉持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的原则,我一路等待着可能的传教,可直到车站他也没有开口。临别时,年轻的牧师在夕阳下向我挥了挥手:“亚伯拉罕曾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一路顺风,我的兄弟。”
将一切人和事理想化是危险的。虽然写下的都是感动和温馨,但我也同样遇上过坑蒙拐骗,遇上过茫然和不知所措。生活不一定处处是美景,可也正因为这样,它才会继续下去。
写下这些文字,回忆起山东的点滴,唯一感到不当的,是离开时太过优柔。我后来读到世界第一位女飞行员柏瑞尔·马卡姆的传记,她说:“如果你必须离开一个地方,一个你曾经住过、爱过、深埋着所有过往的地方,无论以何种方式,都不要慢慢离开,要尽你所能决绝地离开,永远不要回头,也永远不要相信过去的时光才更好,因为它们已经消亡。”未来因为隔着距离而令人生畏,过往因此在回忆的装点下显得温馨。
不过我也偶尔会想起青州的云门山上。那天白雾迷蒙,青翠的山头恍然不可见,可真当踏足其上,一切又都云开雾散。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