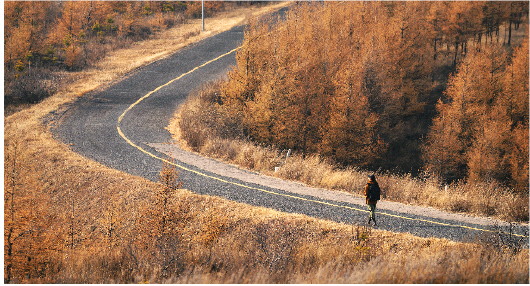□火锅
儿子荷包18岁生日这天,中午做了他爱吃的家常菜,吃了他想要的巴斯克生日蛋糕,然后他陪我去爬山——十三四岁后他就很少和父母一起做这类活动了。下山后,我们去大明湖附近吃饭,吃完后在湖边走了一圈,又步行到护城河,沿着河走到黑虎泉,坐公交车回家。其间我们一直在聊天,说了许多许多话。
■朋友
荷包讲,小学时候有件事曾让他有点难过。好朋友过生日,开party却没有叫他,他打电话过去祝朋友生日快乐,还不解地问:“你为什么不叫我呀?”当时我在场的,似乎他不解的表情和萌萌的童音现在还在跟前。我有观察过他,他看起来没怎么把这事放在心上,而且很快就开心地玩别的了——没想到他会记这么久。他说,小学阶段交朋友经常受挫:过生日的这个朋友觉得他幼稚,不想和他玩;另外几个朋友喜欢聊游戏,而我不允许他玩游戏,所以他们和他没话题。他拼命想融入大家,在大家聊游戏的间隙努力找话题,但他们总是敷衍他一下,然后又开始聊游戏,甚至上学、放学的时候也故意躲开他。他说他当时懵懵懂懂,不知道如何表达这些感受,甚至也不知道它们需要被表达出来。他日后在成长中慢慢记起了它们,并发现它们沉淀得很深。
荷包小时候,我为他写了一本书《为荷包记》。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荷包到底算不算是大孩子》的第一句话是:“荷包快要八岁了。”在书里,我描写的荷包的世界是天然的天真和良善。书结束于他八岁,也许是不得不结束,因为八岁之后生命中的某个基调不复存在,再继续写的话,原有的语调、框架都不再适配。我的另外一个发现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记录,都只不过是外来者的叙事,哪怕这个人是从她的身体内诞生的。这些叙事是令人存疑的,因为它服从于记录者的先行观念和固有认知,就像文人写的田园诗。
荷包初中以后交到了很多好朋友。这次过生日,他分别和初中同学、高中同学聚会,玩得很开心。尤其是高中同学,很多都已经离开学校,毕业后更是各奔东西,再聚不容易了。我问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分开,会不会感到难过?荷包讲,难过是有的,但是没关系,因为他自己已经完整起来了,他永远是带着完整的自己在世界上独自生活。他说:“如果是现在的我,不会打电话去问为什么。我也不会努力去找话题。我就一个人呆着也很好。”
■游逛
我带着荷包爬了我经常爬的山,他像小时候一样不知不觉手中就多了一个树枝。我告诉他我在这个山里都遇到过哪些人、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他听得津津有味。走到一个安静无人的山谷,我讲我经常在这里晒太阳,他就开心地坐下来;我又讲我在这里遇到了群狗,头狗冲我不停吠叫,还围着我转圈,意欲攻击——荷包就气愤地挥舞树枝。下山的时候我们果真遇到了群狗,荷包对它们龇牙齿,意思是“以后不要欺负我妈”。
吃过饭后在大明湖附近溜达。冷清的地方有女人在卖各种小灯笼和冰箱贴,一个箱子,打开可以卖货,提起来随时可以走。冬天天冷,我穿着又长又厚的羽绒服,不停地走路,还是冷。有个卖货的女人在接老公的求助电话,对方大概是问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女人细细地讲了,又抱怨:“你这个人就是不长眼睛。”“没人买东西,不过我再站站,10点关灯我就回去。”
夜晚的大明湖畔非常有市民气息,遍布小规模的广场舞,年轻一点的就凑成一个圆圈踢毽子。零零星星有人直播,唱歌的居多。有一位老叔叔穿着亮闪闪的衣服跳舞直播,好多看客鼓掌。老叔叔跳的每个动作都富含非常精准的网感。我和荷包经过一个广场舞小分队,四五个人排成一队,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领头大姐一个转圈,正好和我脸对脸,那大大的笑容显露出极致的开心。我顿时羡慕起她的愉快,也对着空气比划出两个动作,荷包骇笑着连连后退。我说:“为什么我就不能跳?”“这是她的爱好。”荷包说,“你没有你自己的爱好吗?你在你的爱好里还不够愉快吗?”
我们又路过一个公共健身场所,这里是大爷们的天下。我坐在一个推举器上试图推一下,把手纹丝不动,荷包则轻松拿捏。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得意,就看到一位大爷把把手举得仿佛安装了弹簧一般。有个健身王者抓住杆子尽情地做体操动作,一群人围着拍视频,我和荷包也看得两眼发直——真的是开了眼界,我以前只在小视频里看到过这样的奇观。一位大爷站在我们身边,观察我们的表情,然后适时地给我们传达信息:“这个人六十四岁了。”他耸起鼻子,表达对那一身腱子肉的赞美。
我们一路走到护城河,沿着护城河走到黑虎泉。这条路,荷包小的时候,我经常带他走,他看到青铜雕刻的大老虎,还是忍不住走过去抚摸把玩,只是不像小时候那样爬上爬下了,但看得出他手痒脚痒,在狠狠地控制自己。我说,小时候带他玩,走到这些地方永远走不动,比如在千佛山爬石头大象,来来回回爬一个小时。我总是徒劳地指着各种植物给他看,告诉他“春天来了”或者“秋天来了”,他充耳不闻。荷包说:“我现在能感受到四季和自然了。”“我们学校的天空非常美丽。早饭或者晚饭的时候,我常常指着天空的彩霞让人看,他们都不理我。”“我也能看到我身边经过的人,并且对他们感兴趣。”
■生命的两端
小时候,荷包一直觉得所有的亲人都最爱他。但他其实和我姥姥没那么熟的,因为他出生时,姥姥就已经非常衰老了,何况姥姥又有那么多重孙辈。有一次我坐在姥姥家客厅里和人聊天,荷包满屋子欢乐地蹦蹦跳跳,我说姥姥最爱欣欣表妹,被他听到了,大吃一惊:什么?老姥姥最爱的人不是我吗?然后继续蹦蹦跳跳,可能觉得大人在故意逗他、在开玩笑,最爱他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这是我能想到的姥姥和荷包最相交的一个点。
陪着孩子长大一次,已经遗失的生命源起时的一切不知不觉重新进入记忆之中。那些记忆,本来已经非常遥远,总是笼罩在黄昏将近的夕阳中,而且是超大的远景,怎么也看不清。而看孩子和看幼年的自己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客体,又都是自己。我对照着孩子的刻度,重新调整了我的生命刻度。关于生命、时间到底是长还是短,我也有了新的判断。
生命是一个旅程。姥姥展示给我生命或者天涯的尽头,孩子又告诉我永远有新生。轮回也许不是指一个生命的轮回,而是若干生命组成的图景,这图景无穷无尽,不停不休。
(作者为文学博士、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